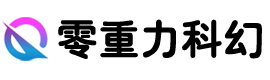作者:子平
责任编辑:旅鸽
导读:洪水暴发的十五年后,敬二于自己的船上接待传说中的渔王,也在渔王的孙女身上看到过去的影子;而在远隔万里的喜马拉雅,敬二的弟弟智江则苦苦思索该如何证伪末日论,但接踵而至的灾难会将所有人拖入地狱……
毗湿奴化身为鱼,以夺回吠陀。洪水退时,他杀死马颈,还吠陀于梵天。
——《圣典博伽瓦谭》
壹
“鲸鱼浑身是宝。”冈畑敬二做了个邀请的手势,他们面前摆着两片鱼肉,“二战最艰难的时候,我太爷爷一辈违反了禁令,渔民们开始重拾捕鲸。为了生存,这没办法。”
汉斯牵强地笑了笑。他努力地睁着老花眼,想确认sashimi(1)生鱼片里没有寄生虫——这是捕鲸人的叫法。尽管无端揣度很没礼貌,但他已经有三四十年没尝过鲸鱼肉了。
在秘鲁,消费野生鲸鱼肉一直是违法的。
“战后百年里,捕鲸事业数起数落。对我们而言,这已经不是肚子的问题了——”冈畑顿了顿,压低了声音,“这是文化。”
“就像几内亚草原的狮子。”汉斯说。
两人哈哈大笑,船也跟着晃。汉斯呛了一下,猛的咳嗽起来。玛缇娜丢下叉子,帮他抚背。
“注意些,老英雄。”汉斯止住了咳嗽,缩回了椅子。衣服已经湿了一半。冈畑倒来一杯水。“乌龙参茶,兴安岭产的。试一试。”
这是个干练的亚洲男人,汉斯留意到他腕带上的锈别针。汉斯尝了一口茶水,味道和咖啡不太一样。冈畑继续了他的故事:“无论是狼还是狮子,都有它们的使命。我们也在寻找自己的意义。你还有使命吗?”
汉斯扇了扇风,他感觉有些闷。今年不止是湿,还很热。他有点中暑。
“我已经很久没出海了,久远到塔拉拉的年轻人都不记得我了。曾经的沙丁鱼产业是我们捕鱼人的天下,如今已经被捕鱼集团取代了——我对大海的使命已经结束。整个传统渔业也是如此。我现在唯一的念想——”他看了看玛缇娜。女孩的皮肤晒得金黄,修长脖子下是丰满的胸脯。已经开始散发女人的魅力。“就是拉扯这可怜的孩子长大。”
“她很漂亮,还有个英雄外公。运气不会太差的。”
英雄。这个词有点刺耳。
玛缇娜放弃了口中的鱼肉,打量着舷窗。她留意到窗台上的石头,像鸵鸟蛋一样大。
“这是沧龙蛋,白垩纪的海洋霸主。智江送给我的。”冈畑敬二为她解释,“我弟弟希望云岛丸像沧龙一样,在海上通行无阻。事实也是如此。”他为汉斯添了杯酒。“我们的船遭受飓风重创,以为就此弹尽粮绝,死在大堡礁的路上。没想到洋流居然带我们反向漂到了秘鲁,见到了不起的汉斯。这不是命运的安排,还能是什么呢?”
“是巧。”汉斯看向玛缇娜,“吃饱了?”
玛缇娜点了点头:“我想休息一下。”
“你如果喜欢,可以让冈畑叔叔留我们在船上待几日。”
玛缇娜瞪大了眼睛,兴奋地点了点头。显然恐龙蛋吸引了她的兴趣。
“今天是玛缇娜的成人礼。”汉斯向冈畑解释,“我想让她足够惊喜。”冈畑敬二愣住了,旋即惊喜地恭喜玛缇娜。玛缇娜礼貌地道谢。她站起身,有力地拉起汉斯的手。
汉斯趴到玛缇娜肩上,左裤管空落落的。
好汉不提当年勇。
玛缇娜想听外公的传奇时,汉斯向来是这么回答的。等成年了再告诉你。
玛缇娜对那个传奇并没有兴趣。每一个年长的旅客听到“了不起的汉斯”,总是双眼发亮,把故事从头到尾讲一遍。她想听的不是了不起的汉斯,是外祖父汉斯。
“今天没胃口吗?”汉斯敞开衬衫,拿着一瓶药水在鼻口嗅。他向路过的船员尽量友善地笑。
船员视线始终在玛缇娜身上,玛缇娜回以一笑。
“没兴趣。鲸鱼肉又硬又干,我宁愿选择羊肉。”玛缇娜趴在护栏上。她刚从水里上来,湿润的皮肤闪闪发光。
“外公,今天我成人了。我可以听那个故事了。”
汉斯的笑容僵了僵。他感觉有点闷,四处望去。得整理一下思路。
太阳不是很大,冈畑敬二的船干净漂亮。船右边是一块挡浪的礁石,当地人称之为卡波布兰科角。红白相间的灯塔从礁石后拐出来。那座灯塔正在掉漆,它和玛缇娜一样大。礁石脚下是贫瘠的沙土,路边列着一排蓝白相间的房子,两艘游船翻在淋浴间外边。卡波布兰科,他逃避命运的居所。
他逃离了名誉,可是得到了什么呢?汉斯问自己。冈畑敬二放弃了日本舒适的生活,在大洋中搏杀。了不起的汉斯,海的儿子,却一败涂地。
好汉不提当年勇,更何况那个故事并不感人。汉斯叹了口气。
“记得《老人与海》吗?那个美国人写的,海明威。”玛缇娜点点头,挂着胜利的笑。
汉斯曾经是秘鲁的渔王,安第斯西岸所有渔者都听过他的名号。他蝉联过世界海钓锦标赛五次冠军。十五年前那个秋天,汉斯还能单独出海,陆地信风和今年一样弱。所有人收成都不好,可汉斯相信自己。只有捕到足够多的鱼,游客和鱼粉厂主才愿意支付酬劳。他是傍晚出海的。
当时洋流和往年不同,湍流突袭了渔船,汉斯失去了方向。他在海上漂了十五天,为了活命,他不得不与鲨鱼、乌贼群和海浪搏斗,还失去了一条腿。死珊瑚、发臭的海面、暴雨和干裂的太阳,尿液,疼痛、饥饿和感染。这是他失去意识前最后的印象。他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被人救起。因为圣地亚哥的双关与渔王的名人效应,媒体对他大肆报道,独腿汉斯变成了不起的汉斯。
“没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了。人民需要一个英雄,我符合条件。那年西海岸暴雨,所有城市都在内涝。渔场和城市都损失惨重。”玛缇娜垂下了眼睛。后面的故事她都知道了,她父母也淹死在洪水中。她是被人从母亲的手里抠出来的。
名声大噪的汉斯不堪烦扰,对世俗感到厌恶。他选择了逃离,在卡波布兰科安顿下来,和孙女住在大海边。他把女儿葬在了海里,不再打算离开了。这个要了她命的地方。
玛缇娜扑到他怀里,大声地哭。
汉斯叹了口气,他拍着孙女,望向海面。腥臭的海面上浮着塑料的垃圾,浮油的浅滩露出了盘结的珊瑚。
骷髅的珊瑚。
贰
暴雨下了三天整。雨水从石阶上溅进门缝里,驱走了一点腐木味。避水的鼠在房梁上吱吱地叫着,库玛丽无暇顾及它们。雨若再下两天,她得考虑逃出饿鼠的避所。下山得花一整个白天,更何况现在这大雨。
天降大雨,是为不祥。
库玛丽无心祷告,她忧心忡忡地望着外边。山上有恶兽的传闻。这扇门年久失修,连野狗都挡不住。
“啪。”
什么东西敲在门上。
“啪啪啪。”声音更沉更急了,墙外窸窸窣窣,仿有人声。
不可能有人,深山老林,没有人会在这时造访神庙。她翻开经书,昏暗不清。她有神祗庇佑,大神曾有预言。大雨、森林、咒言、模仿人语——
“啪!”门锁猛的崩开,攒动的影子在外摇晃。库玛丽掷下经书,到神像后翻找。剪刀、纸钱、她换了个抽屉。快,快快,为什么找不到武器。她摸到了凉凉的东西,一把铳,子弹带倒一地。
来后边了。塞弹、保险,不能乱。开关在哪?
到面前了,要抢先。
“哈!”库玛丽大喝一声。一人半高的黑影在面前晃动,她心里一紧,闭眼拉下扳机。库玛丽肚子上挨了一下,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炸声。她双手发麻,被什么东西扑倒。一张漆黑的脸,库玛丽绝望地尖叫挣扎,阎摩扼住了她。感知在抽离,神啊!皮肤发麻、烫、黑暗。死。
库玛丽醒来时,坐在火堆前。一个人在掐她人中,另外还有两个人。
“你醒了。”面前的人说。
另一个人叽里咕噜说些什么。中国人长相,眼镜片丢了一块,他里边的衬衫被撕开,缠着手腕。外边的大衣也湿透了。另一个人顶着红色的脸,叉手看着她。一群狼狈的人。库玛丽看向眼前的年轻人。
“阿婆,他说抱歉打扰到您。我们同伴生病了,快没命了。”
库玛丽这才注意到第四个人。一个人躺在墙角,意识不清。地上很湿,她望向屋顶。被她开了个洞。
“救人要紧。”几个人扶起库玛丽。
是个清瘦的白人。高高的颧骨,乱蓬蓬的胡子太久没打理,显得更加消瘦。他双眼紧闭,眼珠在乱转。额头很烫。
“是害了疟疾。营养不良,水土不服,山蚊子一叮就不行了。我这有药,过了今晚就不危险了。”
众人脸色缓和了。
红脸的高个子抽出枪递给她,库玛丽一把夺过。大家哈哈大笑。
似乎也没那么可怕。
冈畑智江坐在篝火边,他的外套挂在一旁烤,左手的伤还在隐隐作痛。没有病倒,还有热水喝。尽管屋子潮湿骚臭,浑身酸痛,但总算捡回了小命。处境总归会越来越好的。
他得尽量耐心解释自己是科学家,而不是歹徒或间谍。眼前这位老妇人看上去和蔼,但他得小心应对。她是最后的稻草了。
“我是地质学……和气象学家,”冈畑智江从包里掏出一枚化石,塞到妇人手里,“挖掘,发现秘密。”
妇人露出好奇的神情,他暗暗松了口气。虽然地质学家的身份更吸引人,但严格来说他从事的是气象学。挖掘地质,研究曾经的气候变迁,发现气候的秘密。气候的焦虑已经在学术界弥漫了五年,他的任务是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金钉子寻找证据,否认学术界的猜想。
“发现天气的秘密。”冈畑智江压低了声音,关键时刻必须保持神秘,“像大雨的秘密,早就在石头里写着了。”他捧出一块页岩,画着血色的记号。“这块石头是自然的史书,记录着远古气候的变迁。人类诞生之前。只要我们确定这几个点的特性,就能知道未来的答案。”
助手接过了样本。火药从他脸上掠过,所幸只是烫红。像过火的螃蟹。
库玛丽瞪大了眼睛。她走到冈畑智江面前,跪下点了点他的额头。智江没有抗拒,他困惑地看了向导一眼。
“她说这是向祭祀打招呼的方式。你也是毗湿奴(2)印度教三相神之一。梵天主管“创造”、湿婆主掌“毁灭”,而毗湿奴即是“维护”之神。的追随者,是义人,是智者。”
冈畑智江有些哭笑不得,怪不得宗教总是颇有市场。面前的妇人和向导身边的可怜人一样,天真地陶醉在虚构的世界里。
他不是祭祀,只是一个学者。
你们怎么来的?妇人又问。
“我们从西边过来,在克什米尔遇到了这个可怜人。他是个苦行僧,复古主义者,穿过伊朗和巴基斯坦步行来的。”
向导挠了挠头,磕磕绊绊地说完了翻译。
伊朗。库玛丽重复了一声。
在打仗。她指了指西边。智江想应该是的。
“是啊,在打仗。”
智江忽然悲伤起来,他住了口。
连这位老妇人都知道人与人的战争,那她知道人与天的战争么。如果此行验证为真,那么,那么……他忽然想到在太平洋捕鲸的哥哥。
智江不敢往下想。他闭上眼睛。
叁
汉斯到找到冈畑敬二的时候,他在对付鸟粪。
“缇妮睡了么?”
“是的,哭累了。”汉斯躺到他的凉椅上。
这椅子又冷又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
“讲明白了?”冈畑敬二从抽屉里抽出两瓶酒。他只穿一件干净的水手短袖,壮硕的胳膊上留着一道长疤。他留着干练的寸头,一笑就是一脸皱纹。敬二正值壮年,丝毫不显老态。
“我只能喝一点。”
敬二没有说话,只是笑。他打开瓶盖,浓浓的酒香爆开。“白鹤。”
“你这小子。离开我女儿后还是这副德行。”
汉斯笑骂着接过。酒精从鼻腔里往上涌,钻进脑门。干涸的胃渴望地痉挛了一下。“我只能喝半瓶,剩下的归你。”
“我还有。”敬二拍了一下抽屉,“小小地动用了私权。”
两人大笑,碰瓶。“她知道我是谁吗?”
汉斯摇摇头,陷入了沉默。悲伤爬上了眼前男人的眉梢,他的眉头轻轻拧起。
敬二这个孩子和伊耶塔相识于塔拉拉的酒吧,和他的女儿走到婚姻的门前。他为人机敏,深得汉斯赏识。他富有野心,不仅想当渔王的女婿,还想当渔鲸的王。玛缇娜,小战士,海洋的勇士。冈畑敬二在鲸鱼运动的高潮退掉了婚事,回到北海道的故乡。他的学者弟弟庇护了他。
“云岛丸是我和伊耶塔设计的。”冈畑敬二望向甲板,船长室的窗户被擦得锃亮。“她说过的,我们一起流浪,逃离这个世界。”
他们却逃离了对方。冈畑敬二驾着云岛丸回到卡波布兰科时,伊耶塔已经和当地的一个漂亮小伙成婚。伊耶塔按大和礼数接待了他,他却毫无风度地转头就走。敬二再次赶来秘鲁时,伊耶塔已经被葬入大海。她和洪堡德的鱼群一起,奔流向西,追到北海道方才停歇。
从此,冈畑敬二也再没离开过海。
“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她会留在这里。”敬二猛灌一口。
“悠着点,孩子。”我不能再喝了,汉斯心想。“大洋的热流裹挟南下,沙漠里下起了暴雨。那年没有吹掉雨云的大陆信风,这是天灾,无能为力。日子总得过下去,不是吗。”
“我都懂,老家伙。伊耶塔为什么留在这天杀的沙漠里。要是她也出海,要是我劝动她、劝动你们一起,要是……”敬二大着舌头。汉斯的酒瓶哐当一声掉到地上。
他上去拍了拍汉斯的脸。
“老家伙,老渔王?嗬。真老啦。”
敬二捡起汉斯的瓶子,踉踉跄跄往外走。此时天黯淡无光,海风猎猎,旗帜直往陆上刮。他又灌了口酒。“伊耶塔。”
“不明白。”
玛缇娜觉得很不舒服。
潮闷,气闷。她有点冷,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整个房间是昏暗的,湿风从门里灌进来。天花板是钢管搭的,泛着冷硬的青灰色。身上一股酒气,什么人在亲她。
麦克?玛缇娜抬起头,一张中年男人的脸。
那个奇怪的亚洲男人。他头发谢了一半,像剃了毛的野狗。脸上肥肉是耷拉着的,在蹭她皮带。
“不,不可以。”
外边忽然瓢泼大雨。今天是成人礼。玛缇娜想推走他,手被反扣住,吓得甩开。不可以。男人压在身上,动弹不得,难以呼吸。不能。救命!声音被潮水盖掉。玛缇娜想到恐怖的结果。
船一个颠簸,男人滚下了沙发。玛缇娜见机冲向门,船舱又是一歪,她斜斜地倒下去。男人追上来,砰地关上了门。她又被压在地上。
不可以,冈畑叔叔。她奋力哀嚎,咆哮像被困的母猫。她脸上挨了一下,天旋地转。她有点想吐,软绵绵地被拖开。
短袖被撕开了,男人划伤了她手臂。她挣着双手,蹬开腿。全不能动,被绑住了。她瞪大了眼,老男人流着鼻涕、口水和眼泪,又腥又臭。伊塔。他叫着,剥开了她的比基尼,一口啃上乳房。
疯子!玛缇娜死命躲着,裤子被扒开。她绝望地仰起脑袋,泪水喷涌而出。疯子。操你妈。不可以!外公啊。
伊塔,我好想你。
冈畑敬二进入了她的身体。
肆
库玛丽惊醒了。
夜里几番折腾,她刚才眯了一下。天还没放亮,身上黏糊糊的。有点冷。
可怜的年轻人已经醒了,科学家在喂他水。日本人留意到她。库玛丽坐到火边添柴,白人吃力地抬起头,向她表示感谢。
在冈畑智江看来,丹尼尔不能称作僧侣。苦行者的知识涉及历史、宗教、语言学、哲学和神学,信仰神,却拒绝皈依任何宗教。智江从战俘营买下的丹尼尔,当地人把他当做落单的野狼,来自基地、塔利班或者伊斯兰国。
智江一直不理解,丹尼尔为何执着于日薄西山的宗教。耶稣、安拉、佛陀还是列宁?无所谓,都是过去式了。这是世俗的时代。
历史是轨迹,神学是源头。人们沿着轨迹向前走,逐渐忘了来时的路。丹尼尔如是回答。他只是选择了自己的使命,让人们看清脚下。
又是自己的使命,和哥哥一样倔强。
智江忧虑地望着雨势。丹尼尔抖动着苍白的嘴唇,似乎在说什么。
迈特斯厄……
智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屋里立了个奇怪的神像。上半身是个漂亮的印度男人,下半身是鱼。他头戴珠宝,四个孩子扑在身上。看起来是笑,其实是在呲牙。
“马特斯亚。”库玛丽纠正丹尼尔。
丹尼尔开心地笑,显然是庆幸脑子没烧坏。他看向冈畑智江:“我讲个故事。”
智江没好气地喂了他一口烫水。
漫长的前行,人经历过无数危险。种族、文化亦或是精神。但主最终选择了人,至少暂时是。
主示意先祖,借方舟逃离巴比伦,庇于亚美尼亚的亚拉腊。文明的种子得以保存,启蒙的光辉撒向世间。六个千纪以来,苏美尔、古埃及、先亚述、波斯与罗马,闪耀的辉煌终被埋葬。上古的余音消散,残留在神话里,渗透到文明的角角落落。
文明是共通的。创世纪与诺亚、大洪水与摩奴。主的信徒在西方行走、相互仇恨,最终输掉了世俗;东亚和南亚更只有模糊的谣言了。这个开放时代,信仰反成了愚昧与顽固的代名词。
“何必执着于过去,世俗的时代很好。”
“人正在堕落。”丹尼尔面带嘲弄,“就历史而言,忧患带来的是希望,安乐是死亡的预兆。月球能源、无人化生产、虚拟社交和享乐主义,欧美和东亚和平太久了,已经烂到了骨子里。总得有一件事来敲醒人们,宗教、战争或者基因火药桶。”
“你选择了宗教的戒棍。”
“我只是做了最好的选择。防范未然,避免灾祸。”丹尼尔睁大眼睛,映着闪亮的火。
“神谕是碎片,零落四散,在各地异化。人们总以为自己的是对的。希伯来圣经、新约、古兰经和梵书,各自有无数的信徒。这些都是神谕的拼图。我要补全它们,向世人展现一个完整的、值得追随的神谕。这个神谕将会约束人与机器,协调忧乐,重新规范前行之路。”
“你想当耶稣?”
“我只想当孔子,一个整理者。”
“可你来了印度。”智江搜肠刮肚,疲于应付。
“我从希腊渡到埃及,借道叙利亚,穿过伊朗。可惜全都毁了。城市化、商业化和现代战争。只剩尼泊尔握着最后一块拼图。古印度是印欧语系的源头。
![]()
你知道的。”
“你找到拼图了吗。”
“找到了,在昨夜。”
智江遗憾地看着他。就心理学来说,眼前人最终还是烧出了妄想症。
丹尼尔望着雕像,虔诚地笑。
“鱼灵马特斯亚,毗湿奴的化身。在印度的宗教里,佛陀也是毗湿奴的化身。毗湿奴的存在从吠陀时代延续到今日:《百道梵书》、《摩诃婆罗多》到《罗摩衍那》。蓝毗尼让我失望了,佛陀诞生地成了商业城;但这个小庙没有。毗湿奴果然是上帝。”
“大神有过预言。”库玛丽的声音很小,智江这才想起她。她一直捧着手机,在听实时翻译。“世界濒临破灭,末法现世结束之时,毗湿奴将手持利剑,身跨白马,化身为柯奇现身救世。”
冈畑智江放声大笑。
丹尼尔看着他,没有打断。“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与你同行吗?”
智江笑不出来。他告诉了丹尼尔此行目的,证伪一个气候猜想。丹尼尔跟了他走。
“你现在还坚持世界末日不可能?”
“可能性不大。”冈畑智江抚了抚眼镜。模糊的左眼让他很不习惯。“根据推算,在造山运动之前,我们的岩石样本属于平原。曾经有五次,气温比现在温暖——我们都做了标注。大水不可能发生,等我的海平面判断便是。结果出来,所有谣言不攻自破。”
“那边在打仗呢,伊朗有核弹。”丹尼尔毫不饶人。“且不说大水的事,要是爆发了核战争,你还能这么乐观吗。人如果无法驾驭自己的创造物,只能自食其果。”
“不可能。核弹留下的伤疤——”
“老师!”李打断了对话。智江不快地看去。
助手手里捧着岩石样本。头戴笨重的显微镜的他,像丑陋的矿业机器人。智江走向李。页岩上画了五条红线,好像手指拉出的血迹。
伍
汉斯看向胳膊,刚刚被挠出五道抓痕。伊耶塔盯着汉斯,双目通红。
为什么丢下我们出海,现在你满意了吗。了不起的汉斯?
一箭穿心。汉斯又回到了噩梦般的那几天,天下暴雨。他在悲伤的海洋里流浪,吞咽着泪。他不想解释,只想再看一眼。再多看一眼。
世界翻了一页。
咚。汉斯脑袋磕到什么。伊塔。
这一摔真结实。他头昏眼花,酒醒了。
整个船在颠,外边下着大雨。像十五年前一样大。
汉斯眨了眨眼。同样是鱼群稀缺、奇热。现在多了大雨。
日本的客人不知道去哪了,窗外的旗像落汤的鸡。雨点像冰雹一样砸下,噼里啪啦。汉斯爬起身,右腿的关节在疼。去你妈的痛风。汉斯披上雨衣,扶着门外的扶手。他一个激灵,真冷。
水手们在甲板上跑动,雨跟着海浪的方向往岸上拍。变天了。汉斯逮住一个年轻人,你们船长呢!
不知道,水手回答。汉斯内心大骂,他担心昔日的准女婿掉海里去了。
下暴雨,他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疼,人总是善忘的。吃白饭的政府无力普及排水系统。洪水马上就会来,该死的洪水。船马上就得拔锚,不管去哪,总之不能原地等死。
他也许知道敬二在哪。抓住扶手,往前跳,脚下一滑。汉斯大骂,就没人来搭把手吗!海在翻,人们在雨里飞,没有人理会他。先找玛缇娜。他裹着雨衣,抱紧扶手,往二楼货舱走。那里是安顿他和玛缇娜的地方,伊耶塔最喜欢的秘密舱室。
撑、跳、滑。你妈的。撑、跳、滑。
门打不开,他掏出钥匙。要是你在里边,老夫剥了你的皮。又是一阵风,雨水灌到他靴子里,老汉斯一个激灵,打开了门。一股腥暖的风铺了出来。
玛缇娜!汉斯高叫,他适应了舱室的光线。又是一颠,他滑了一跤。地上倒了一堆东西,把手有血迹。是搏斗的痕迹。汉斯心里一沉。抄起一个瓶子往后挪。有人在打鼾。玛缇娜出现在眼前,他险些晕了过去。
宝贝孙女被反绑在支撑柱上,一个水手趴在地上。她无力地跪着,衣服被撕烂了,乳房被掐得紫红,凌乱的头发盖着脸。
玛缇娜。
老人颤抖着扑上去,去够她鼻子。还好。有呼吸。刺鼻的酒味,男人斜斜地趴着,露着恶心的生殖器。玛缇娜裤子被褪下,下体肿得通红。心在滴血,汉斯怒盯着男人,气得呼吸不畅。他可能会死,肯定不会比这恶棍早。
他举起瓶子,对着下体奋力一砸。
鼾声塞住。男人一个抽搐,猛的蜷缩起来。他捂着下半身,开始大声哀嚎。汉斯浑身发颤,他走上前,脸在抽动,模糊了眼睛。这个畜生。再举瓶,那人翻身打滚。
冈畑敬二。
汉斯一惊,酒瓶落了空。手臂震得发麻。冈畑敬二挣扎着痉挛,血渗了出来。他在嘶吼,要把肠子呕出来似的。
船又是一颠,天花板晃了晃,冈畑没了声。
怎么会是……冈畑睁大眼,发现了伤势,血淌到地上。汉斯提瓶坐在面前,后边是赤裸的昏迷的玛缇娜。我……
“出去。”汉斯低吼,像垂死的雄狮,“洪水要来了,快拔锚。”
船跳了一下。冈畑敬二撞出了门。
玛缇娜!只要活着就好。
汉斯捧着孙女的脸,伸手去解绳子。手腕勒得通红,是一道道血痕。吧嗒,眼泪滴下,玛缇娜疼得一抽。孩子,我可怜的孩子。
船猛地翻了个跟斗,椅子砸了过来,不要。老汉斯护紧了孩子。所有东西忽地腾起,世界失了声。水在翻动,没了雨。外边隐约无数尖叫,亦或者尖啸。船体又一震。
地板挣扎而上,压得骨头嘎吱作响。
碎衣服和血迹在黑暗里混合。窗外没了水。淤泥,裸露的海床和垃圾。海水全部撤走了。另一边是斜斜的海面,陆地在倾倒。一堵墙,百米千米,搅动着平缓盖来。空间在折叠。
安第斯在溃败。沙漠、灯塔和白船,裹挟着一切。呼啸,奔向大海。
我的神。
巨啸拍到了眼前。砰然。
不。玛缇娜,别。磕着脑袋。嗡。
陆
世界末日?绝无可能。
情况有点复杂,他不好判断,助手告诉冈畑智江。李手忙脚乱地打开投影,左右对不上焦。智江有点烦躁,不该被丹尼尔干扰的。
当今的人类,如日中天。殖民月球,虚拟现实惠及80%的人口,下一个核能革命正在眼前。世界末日就是用来骗小孩——还有圈钱——的玩意。科研的任务就是为人类谋福祉,顺带震慑宵小之徒。冈畑智江失去耐心,接手了工作。
对好焦,参考面在右侧。右移,打光。
根据计算,这块样本的海拔高于新加坡。按照南极钻取冰芯的结论,其时温度与现在相仿。样本的地貌应当属于平原。确认古海岸线,打消学术界的焦虑,正是他此行的目的。若是样本检测结果为海洋,则意味着乐观派的失败。超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海洋生态恶循环、气候异常与农业破产。南太平洋的特大开尔文波会掀起海啸,他的哥哥将生死未卜。丹尼尔末世预言第一步的实现。
无论如何,可能性极小,和存在上帝的可能性差不多。调笑归调笑,冈畑智江对严谨的计算有信心。
助手调高了激光亮度,清晰的图像跃到墙上。赏心悦目。
样本里布满了小点。冈畑智江前后微调,密密麻麻的小点出现眼前。每次看虫点,他总会起一身鸡皮疙瘩。螺线形,一二三……四五,五个瓣,截锥圆辐虫。还有黑色线体,放射虫。全都是。
移到另一个地方,依旧如此。
海洋古生物。
冈畑智江抬起头,助手脸色灰白。屋子昏沉沉的,雨在发泄,火苗在摇曳。两个信徒窝在火边,陷入黑暗的脸隐隐约约。
李点点头,想法一样。
“这不能说明什么。”智江自知底气不足。
“看来我对了。”丹尼尔落寞地笑,像只该死的鬼狐,“就差一个核弹,我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错了。冈畑智江走到门前。末日假说是对的。空中弥漫着臭氧。哪边在打仗?哦是这边。
大水。敬二……天黑漆漆的。
风在呜咽,声音愈来愈大。眼前一闪,卧倒,他猛地捂住眼。停顿,雨还在下,空白,心脏疯狂鼓动。发生了什么!他寒毛倒竖,毛骨悚然。李在哀嚎,丹尼尔也是。不,应该不是。丹尼尔这个乌鸦嘴!还有向导和老妇人。
看不见。智江拼命睁开眼,是睁开了。
黑的,紫的视界。太阳穴在搏动,酸,眼泪滚了出来。他撑住地上,左手是灼热,是火。
焦味。他闭上了眼。
伽玛射线。来不及了。
紫色世界里蠕动,像是噪音,更像是鬼魅。雨声的方向隐隐有光在闪动。是光,还是噪音。
嗬嗬地笑,丹尼尔低声。“核弹,果然是核弹。我又对了。”他旋而狂笑,“来不及啦!”
冈畑智江匍匐在地上,泥土缠上脸颊,钻入腥红体液的暖流。
© 本文版权归 子平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及合作请联系作者。
(校对:瓦力)
原创文章,作者:子平,如若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