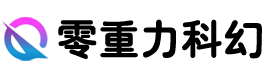第一章:嫉妒
地球在失去最后一块平衡时,仍旧保持着荒凉的庄重。
没有什么盛大的爆炸,也没有紫色的蘑菇云冲破天幕。只是空气越来越厚重,像潮湿的布,缓慢裹住人的呼吸。
城市废墟在夜里闪着黯淡的火光,海洋褪去了湛蓝,逐渐泛出深褐色的浑浊,仿佛正在腐烂。
全球气象中心在倒数最后一百小时的通报里写:
“能源储备不足,人类社会运转进入末期状态。水污染、生物变异、耐药性疾病正同时爆发。”
再没有人去查看这些通报。
所有人都知道,文明的终点已经到了。
在荒芜的平原上,巨大的银白色飞船缓缓升空。它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任何告别,只是一座人类最后的执念。
它的建造耗尽了地球所有可以调用的资源,持续了十年,直到再也无法造出第二艘。
它是人类最后的船。
它的名字在飞船表面,是一串刻意用多个文字拼写的字母:
ARK-216。
它注定只容纳极少数人:政治领袖、科学家、飞船建造工程师、资本巨头以及他们各自看重的随行人员等。
没有人提起过那些从未进入名单的人——包括大多数工人。
他们为飞船铺设过最后一块舱体,也在最后一刻被清点在金属门外。
A是其中一人。
飞船总工程师I亲手在最后一次审查报告上签字时,看到他的名字。
那一栏的备注是:“程序优化特级工程师。”
I的指尖在那一行字上停顿了片刻。
助理小声问:“要保留吗?”
I没有回答。他只是在心里默默想:这个人能力太突出,而且太沉默。
他害怕。
那种害怕不是针对A本人,而是针对一种不确定感:
如果有一天,A变得比我更重要呢?
短短一秒,I把笔尖移开,低声说:“换掉。”
助理也没有再问。
于是名单在凌晨敲定。
飞船启航那天,地平线上最后一座城市在雾霾里微微闪烁。
没有人再哭喊,所有人都明白——这就是结局。
飞船升空以后,舱内的气氛一度接近狂喜。
大厅的屏幕上,循环播放编号R-7-16星球的影像:蓝绿色的旋涡、黯淡的云层,看上去像另一个年轻的地球。
有人在直播频道宣布:“这是人类文明新的起点,是对命运的胜利。”
人们举着香槟,互相拥抱,合影、歌唱。他们在飞船最宽阔的大厅里铺上彩色的地毯,悬挂着各国的旗帜,仿佛终于在太空里达成了短暂的和解。
他们以为,一切都在掌控里。
飞船推进的声响一如既往,深沉而稳定。
第80天在最内层的中控舱,太空局局长B和总工程师I并没有去参加每周的庆祝。
两个人面对一整面透明的操作面板,一行行代码在暗淡的光线里缓缓滚动。
I用手指敲了敲屏幕,屏幕里浮现出进度条:
目的地接近:请准备进入自动减速程序。
I确认了身份,按下了确认指令。
没有反应。
B抬起眼睛看他,眉头微微动了动:“怎么了?”
I又输入了一次。
仍旧没有任何反应。
接着,一行陌生的文字出现在最顶端:
程序变更检测:请验证身份。
I只觉得心脏被一只手攥住了。
他输入了最高权限密码,手指因为不自觉地用力而发抖。
这次,面板中央出现一个闪烁的提示:
当前程序已由特级工程师A加密修改。
如需接近目的地,请输入密码,否则飞船将在150天后自动返航。
B的脸色一点点失去血色。
他们对视了好几秒,没有说话。
不到一小时,五个最高级别的人被召集进中控舱。
C、D、E、F、H坐在合金会议桌的另一侧,每个人都面无表情。
I把记录文件投到桌面上,屏幕发出冷淡的蓝光。
B压低声音:“这是一个事实:飞船无法自行靠近R-7-16星球,除非先输入密码。”
E的声音冷而刺耳:“那就破解。”
I看着他:“这是A留下的程序。他在系统核心层做了加密,除了他自己,没人能一步到位。”
H皱眉:“有没有线索?”
B示意I说下去。
I缓慢地呼吸了一口气,抬头看着所有人:“我们检查了系统日志,有一段指令写着——‘密码已刻在飞船外层的太空舱底部。’”
一瞬间,整个会议室安静得像失重。
C的嗓音哑得几乎听不清:“……他疯了。要先输入密码,才允许解锁舱壁,才可以去看外层。”
“是。”
I的声音很轻,却没有人怀疑它的准确。
这是一个绝对的死局:想看密码,先要解锁;想解锁,需要密码;没有密码150天后自动返航。
第81天,密码学家团队开始封闭式破解。
他们接管了几乎所有计算节点,调动飞船全部备份资料,一遍遍尝试。
舱内广播每天依旧按时播放安抚音乐,向所有人播报“航程正常”。
大厅里,人们还在幻想新世界——他们看不见这些会议室里的寂静。
第98日。
密码学家仍旧没有任何进展。
所有试验的记录,只是一行行拒绝:
验证失败。
验证失败。
验证失败。
当晚,五个人又一次坐进会议舱。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同一种疲惫,像一层逐渐凝固的灰。
C终于开口:“他嫉妒我们。”
E也低声说:“他恨我们能离开,恨我们能不去死。”
F摇了摇头,声音很低:“他其实完全可以偷偷上船,他既然能修改程序说明他有这个能力,但他没来。”
“所以他更坏。”E的嘴唇微微颤抖,“他选择让自己留下,然后把一千人都困在这里。”
没人再接话。
桌面上,B揉着眉心,闭着眼睛,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也许他只是想让我们想清楚,何为责任。”
那句话在I心里一点点扩散,带着一种钝钝的痛。
他想起十年前,那个年轻的工人站在合金廊道的尽头,递给他修正程序。
他当时看着对方沉默的眼睛,突然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失去“总工程师”的位置。
所以他把A排除了。
他永远不敢承认,决定不是为了飞船的安全,只是为了他自己心底最深的嫉妒。
一整夜,他再没合过眼。
飞船在宇宙中缓慢滑行,外面的恒星依旧缓慢移动,像一场永不落幕的讽刺剧。
距离播报的自动返航时间,只剩下50几日。
第99天,飞船依旧在宇宙深处缓慢滑行。
外层的恒星似乎永远没有改变过它们的位置,像是某种无声的注视。
大厅里,庆祝的气氛已经淡了。
人们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兴奋。即便是最乐观的人,也在每一次透过观测舷窗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疑惑。
为什么周围的星体几乎没有位移?
为什么飞船广播依旧只播报“航程正常”,却再没有任何新的坐标?
第99天夜里,一个生物学家P站在观测通道的透明穹顶下,目光盯着同一片星空。
他过去三天都在这里,每隔一小时用测距仪记录一次星图。
数据没有任何浮动。
他心里有一种寒意,一点点蔓延。
凌晨,他回到自己的住舱,把三天的观测记录传给了几个同样不安的同僚。
他在群组里留下了一句话:
“我们必须问他们,我们究竟在飞向哪里。”
第100天。
飞船每日例行的汇报会,终于第一次出现了波澜。
P在人群最外沿举起了手。
大厅里数百人安静了几秒,很多人转过头看他。
P抿着嘴,声音沙哑:“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观测星图在最近五天里没有任何位移?”
主屏幕上的大气层模拟画面依旧循环闪烁,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站在台上的D抬起下巴:“飞船正在执行接近程序,这需要调整轨道。”
P的眼睛死死盯着他:“所以你能展示一下轨道调整数据吗?”
周围有人低声议论。
没人动。
几秒后,C走上前一步,平静地说:“观测数据属于机密。请你冷静,P博士。”
“冷静?”
P的声音一瞬间拔高:“你让我冷静?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三个月,没有任何新坐标,没有任何恒星位移,你却让我冷静?!”
大厅里,有人小心翼翼地看向彼此。
几条消息在短短一分钟里同时传开。
生物学家、部分工程技术员、几个科学研究人员,还有几名商人,都收到了P的测距图。
所有数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飞船在近两周,几乎停止了推进。
第101天清晨。
飞船第一次出现公开的质询。
大厅中央的人群越来越多。
没有人再去工作,所有人都等着一个答案。
太空局局长B和政治领袖C、D、E、F、H依次出现在台上。
四周的光线很暗,只有屏幕把几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B握着讲台,嗓音低沉:“……我们没有想欺骗任何人。”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们?”
一个声音从人群里响起,像一把刀划破沉默。
B的手指微微抖了抖。
他闭了闭眼,缓缓吐出一口气。
“飞船的程序被修改了。”
大厅里几乎在同一刻,响起一阵嘈杂的呼吸声。
“修改?”
“是谁?”
“什么叫修改?”
E接过话筒,声音干脆:“一个人,在飞船起航前把程序写进了核心层。我们……无法绕过。”
台下有人爆发出一声干笑:“你们说的是A吗?那个被你们开除的程序员?”
I在台下,他抬头看了看屏幕,没有说话。
他听见有人用嘲讽的口气低声说:“真可笑。一个被排除的人,反倒掌控了所有人的命运。”
嘈杂声一点点蔓延,像一场忽然燃起的火。
“所以我们一直在原地打圈?”
“你们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多久了?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们知道还继续骗我们?!”
大厅里的空气像一锅沸腾的水。
有人拍着椅背质问,有人握紧拳头,有人已经开始哭。
B的嗓子几乎失了声:“请你们冷静——”
“冷静?!”
一个戴着工程师徽章的人站出来,眼圈通红:“三个月!我们坐在这里,看你们每天在会议室里开会,你们告诉我们‘一切正常’,告诉我们‘一切在掌控中’——你们什么都没说!”
没人接话。
E和C在台上交换了一个眼神,没有一个人愿意再看人群的眼睛。
有一阵长长的静默。
所有人的呼吸都沉重,连飞船深处的机组运转声都清晰得令人心慌。
终于,有人声音沙哑:“……所以,我们是不是根本没有在前进?”
B微微颔首:“在减速程序被解锁之前,飞船只会维持恒定轨道,无法接近目的地。”
“你们有办法破吗?”
“……没有。”
“那密码在哪?”
B抬起眼睛,看见台下一张张疲惫又绝望的脸,胸腔里有一种缓慢而彻底的疼。
他只觉得喉咙干到几乎说不出声音。
“密码在飞船外层的太空舱底。”
大厅里,寂静得一秒钟都没人出声。
有人艰难地开口:“那……要先解锁舱壁,才能出去看?”
B点了点头。
短暂的沉默里,P慢慢坐回椅子里,捂住了脸。
一个老年的科学家缓缓闭上眼,声音几乎听不见:“……他不只是嫉妒。”
有人冷笑:“他比谁都明白,这一千人意味着什么。他恨这个飞船,他也恨我们。”
“可他也没选自己上船。”
“那又怎么样?他毁了所有人。”
声音此起彼伏,没有一个答案是确定的。
I站在最外沿,看着那群人。
他忽然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和A对视时,那种冷静又空旷的眼神。
那眼神里没有悲愤,也没有恨,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无法打扰的沉默。
一种比嫉妒更复杂的情绪。
这一天过去,飞船终于不再平静。
人群开始分裂,有人相信这是应得的报应,有人觉得这只是荒谬的意外。
更多人只是沉默,把自己锁在狭小的舱室里,低头看着双手发抖。
夜里,I一个人走在通道里。
飞船在宇宙里悄无声息。
他忽然明白,最可怕的不是密码的失落,而是所有人都必须正视的那个问题:
我们究竟是被背叛了,还是从来就不配得到救赎?
第二章:权力失效
飞船在深空里缓慢滑行,像一颗被遗弃的种子。
大厅那场质询会结束后,没人再提起“胜利”两个字。
一整天,所有人都各自缩回狭小的舱室。只有走廊里的灯在间歇闪烁,投下一格一格昏暗的光。
第102天凌晨,工程组把一份文件交到了太空局局长B手里。
他看了很久,没说话。
I站在旁边,目光落在最底一行数字:
氢燃料剩余:64%
水循环系统效率:83%
合成农场下批收成周期:45天
船上现有食物(维持每日三餐):约70天
B指尖抖了一下,几乎要把文件折起来藏进口袋。但他还是抬起头,声音干哑:“……把数据拷一份,传给所有政治代表。”
同一天晚上,十几个政治家、军事代表、飞船高层齐聚中央会议室。
D第一个说话:“所有人都看到了,资源消耗远超预期。如果我们继续按现有标准分配,45天后就会出现第一次断粮。”
E面无表情:“有些人价值更高,比如基因学家、工程主管、太空导航员,他们必须优先。”
F盯着他:“所以,你打算让谁去挨饿?孩子?孕妇?还是普通技术员?”
E不耐烦地摆摆手:“我只是提出事实。没有合理分配,我们全都死。”
空气里一阵死寂。
I坐在会议桌尽头,眼神空洞。他能看见桌面反光里,自己脸色惨白得像张纸。
他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里什么声音都没有。
会议持续到深夜。
有人提议按国籍分配。有人提议按财富分配。有人干脆提出直接封锁农作舱,把食物交给军队管理。
B撑着桌沿,手背青筋暴起:“如果你们真这么做,所有人都会拼命抢夺。他们已经失去希望,不会再信服任何命令。”
C揉着眼睛,声音干涩:“……那就公投。”
“公投?”
“用他们剩下的信任,决定一次分配方案。至少,不要立刻让飞船崩溃。”
没人再反驳。
第103天,飞船通道屏幕同时亮起一条简短的通知:
“因资源储量告急,决定进行临时公投,投票将在12小时后结束。所有成年乘客均享有同等投票权。”
那天,走廊里没有人交谈。
所有人都在看着那行文字,仿佛在看一纸判决。
第104天,结果出炉。
简单得残酷:
“投票通过方案三:儿童及怀孕女性每日优先供应食物与水。成年女性配额为成年男性的80%。各领域专家、政治代表、资本供给者与随行家属不享有特权。”
没有掌声。
也没有愤怒。
只是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地球已经死了,国家已经死了,所谓秩序也死了。
他们只剩下一艘缓缓耗尽燃料的船。
第110天。
第一个储藏区被人砸开。
有人目击到四个戴着面罩的人,拖走了十几箱罐装营养液。
当天傍晚,军队开始持械巡逻,强制封锁所有物资仓库。
走廊尽头,生物学家P看着那些武装人员,忽然觉得胃里一阵翻涌。
他走到透明舱壁前,隔着深空看那颗已经看了三个月的星星。
它依旧在同一个地方,没有靠近分毫。
有人走到他身边,低声说:“这就是新世界吗?”
P没有回答。
他只是看着那颗恒星,眼睛一动不动。
第120天,走廊里开始有人悄悄交易食物。
一个商人小组用最后的金条,换到几罐浓缩蛋白。
另一个科学家把珍藏的显微观测芯片,换来几袋干粮。
不再有人谈论公正。
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如果再过一个月食物耗尽,自己要用什么去换一口活下去的机会。
第130天。
大厅里第一次出现冲突。
一个男人手里抱着一包蔬菜,身上沾着血。
他在门口站了十几秒,缓缓抬起头,声音像石头一样干:“……我只是饿。”
再没有人敢拦他。
那一晚,大厅的灯一直亮着,没人睡觉。
I半夜独自巡查时,看见一个小孩蹲在储藏舱门口。
他认得这孩子。
是C的儿子,从飞船启航起就因为爱吃而被人暗暗称作“小鲸鱼”。
他习惯每天要吃三顿主餐、两次加餐,还要在睡前喝一罐热牛奶。
哪怕在飞船刚起航的庆功宴上,他也曾把一整盘肉丸都端走,一个人吃得心满意足。
那孩子现在穿着一件白色恒温衣,脸颊还有被擦拭过的油渍。
可他还是在舔——
一小口、一小口,把门缝里渗出的营养液舔得干干净净。
他的动作不急不慢,像在理所当然地索取。
I站在通道尽头,没有立刻走过去。
他忽然想到:
即使这个孩子已经得到了最优先的配给,他还是觉得不够。
这不是饥饿,这是习惯了想要更多。
小孩看见他,抬起头。
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是短暂的愣住,随后又低下头继续舔。
I缓缓走近,看着那张因为撑得过多而微微浮肿的脸。
他想训斥,想说:“你已经分到了足够的食物。”
可什么也没说出口。
他忽然明白,飞船最深处的裂缝,早在他们起航那天就埋下了。
哪怕是孩子,也没有人甘心与别人平等。
第三章:人类共业
飞船在深空里缓缓漂行。
第131天,广播开始发出周期性的预警音:
“请注意,当前食物储量约剩余15%。请全体乘客按分配标准每日领取配给,避免囤积或浪费。”
声音平静到近乎冷漠,仿佛并不是在宣布一次即将到来的饥荒。
同一天深夜,医务舱的灯亮着。
P坐在金属台阶上,手里捧着一罐干粮,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吃掉它。
不远处,另一个工程师蹲着,肩膀缓缓抖着。
“如果我们当时不签署那份转基因商业授权……或许不会那么快失控。”
没人接话。
P慢慢抬起头,看见他眼里有一种快要碎掉的神色。
“当时公司说,这是对地球的馈赠。低成本高产粮食,能救几亿人。可是它毁了所有土壤。”
“是啊。”
一个声音在阴影里低低响起:“我在医药集团做项目经理,我们曾经压下过抗生素耐药性的警告报告。那一年我们赚了三个亿。”
那人喉咙哑得像砂纸:“我妻子也在地球上。她最后发来的消息是,她发烧四十度,吃了所有药都没用。”
没人再说话。
P闭上眼,过了很久才缓缓呼吸一口气:“我研究过海洋修复项目。我们本来有机会扭转潮汐酸化。但被一个委员会否决了,因为——”
他顿了顿,苦笑:“因为他们说,太贵。”
四周没有人辩解。
没有人再说“不是我的错”。
第135天,飞船的走廊开始变得危险。
半夜,一个粮仓的门被撬开,几十袋罐装食物消失。
那天早上六点,C的妻子推开医务舱的门,声音嘶哑:“……有人看见我儿子了吗?”
她的脸色灰白,头发散乱,身上裹着一件睡袍,赤着脚。
最初没人理会。
可两个小时后,还是没人见过那孩子。
传言开始在飞船里蔓延:有人说,看见他昨晚在走廊溜达,也有人说,他被人带去储藏舱“分东西”。
没人知道真相。
直到中午,有人看见走廊尽头那扇老旧金属门,门缝里渗出一条深褐色的痕迹。
那是飞船结构最老的检修通道,几乎没有监控。
当军队破门而入时,里面弥漫着一股铁锈和脂肪混合的味道。
三个成年男人蜷在墙角,双手沾满血,衣襟撕得凌乱。
一个人正用刀把孩子的小腿割开。
他抬起头,声音干涩:“……还没死。”
那表情不是羞耻,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被逼到极限的坦白。
“太久没吃肉了。”
没有人开口。
士兵举起枪,手在抖。
有个年轻军官脸色发白,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这不是我们。”
可没有人反驳他。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正是他们。
那天傍晚,C坐在大厅中央,眼睛空洞。
她没有哭,也没有喊。
只是两手放在膝头,像一尊石雕。
四周没有一个人敢靠近。
P站在走廊尽头,低声对身边的人说:“人类历史上,太多次了。”
“是啊。”
“饥荒、战争、围困,每一次都有人吃人。”
“这有什么区别吗?”
P垂下眼睛:“区别在于——我们都以为飞船能让我们变得比祖先更好。”
没人再说话。
第140天,飞船的走廊再没有了灯火。
再没有人信任任何规则。
第145天,广播响起:
“请注意:距离自动返航还有五天。”
声音和平时一样冷静,却把所有人最后一点希望碾得粉碎。
I走过一间又一间舱室,看见人们坐在床沿,背对着门。
没有人再喊口号,也没有人再咒骂A。
所有人都明白了:
这不是谁一个人的复仇。
这是他们所有人一起造出来的结局。
那一夜,飞船在无声的深空漂流。
四周是亿万年的星尘。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再去。
第四章:良知
飞船在深空里缓慢漂行,像一具失去目的地的躯壳。
第145天,广播第一次发出倒计时:
“请注意:距离自动返航还有五天。”
那一刻,人们坐在各自的舱室里,没有任何喧哗。
有几个孩子问:“返航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回答他们。
大人们低下头,像一群被突然点名的囚犯。
第146天,食物分发变得混乱。
早晨,走廊里排了三十几个人,等着领取每日配给。
军人推着小车缓缓驶过,车上只剩一层塑料包装的干粮。
轮到最后几个人时,士兵面无表情地说:“没有了。”
队伍最末端,一个女人用力吸了一口气,声音颤着:“……昨天我明明看见储藏里还有。”
没人理她。
军人只抬眼看她一瞬,又看向队伍下一排:“走。”
她没有动。
她的手在抖,指甲几乎要抠进掌心。
她身边的男人低声说:“别闹。”
她没理他,缓缓伸手去扯小车上的最后一袋。
刹那间,枪托重重砸在她手腕上。
那声音清脆,像折断一根小树枝。
她捂着手倒在地上,谁也没上前。
同一天夜里,走廊尽头传来敲门声。
C的妻子披着毯子,跑到P的舱门前,声音嘶哑:“你有看见他吗?他……又不见了。”
P一动不动。
他知道她指的是谁——C的儿子。
那个在庆功宴上嚷着要“吃到世界上所有美味”的孩子。
“昨晚他在我床边,说他饿。”
女人的嘴唇颤抖:“我只给了他一点罐头,我……不够了。”
P慢慢把门关上,没有说话。
他在门缝里看着她蹲在走廊上,用手捂着脸,肩膀一颤一颤。
第147天清晨,C的儿子还是没有回来。
这一整天,走廊里只有脚步声在回响。
有人低声议论:
“是不是……被藏起来了?”
“你胡说什么。”
“你自己想想,一个月没有肉,谁还守得住底线。”
没人再接话。
那句话落下去,像一块石头砸进井里,久久没有回声。
当天傍晚,军队排查每一处舱室,还是没有找到孩子。
等他们查到最后一层检修通道时,灯光已经昏暗。
那扇老旧的金属门,门缝里渗出一条深褐色的痕迹。
那一夜,走廊没有灯。
谁也没有睡。
第148天。
广播发出新的指令:
“所有人必须留在舱室,由军队统一配送食物。”
那天清晨,I走过走廊,看见一排排紧闭的门。
有一扇门没关严,缝隙里露出一只眼睛。
那只眼睛没有愤怒,也没有祈求。
只是静静看着他走过去。
午后,第一批配送车到来。
军人把食物一袋袋放在门口。
每送完一户,就在名单上画一笔。
轮到一户,没人回应。
军人敲门。
还是没人开。
他弯下腰,把两袋干粮推进去一半,又看了看四周。
迟疑片刻,他把一袋抽回来,塞进自己背包。
那动作极快,像一种早就习惯的动作。
他不知道,走廊尽头,有个人正透过门缝看着。
傍晚,消息传开。
“他们在偷。”
“所有人饿,军队却藏着肉。”
有人再也忍不住。
第149天。
没有广播警告,也没有任何预告。
人群在走廊上聚集。
先是十几个人,接着几十个人。
有人推搡,有人咒骂,有人把箱子踢开。
有人喊:“拿回来!”
“那是我们的!”
“他们凭什么吃肉?!”
吵嚷声一浪高过一浪。
有人举起金属棍,敲在配送车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枪声终于响了。
那声音短促,干脆。
有人倒下。
血溅在舱壁上,慢慢滑落,留下一道狭长的痕。
走廊里忽然静了三秒。
随即,所有人都冲上去。
那一夜,没有人能说清到底死了多少人。
有人说三十,有人说一百。
没有人再去数。
他们只知道,飞船只剩一半不到的人。
等到天亮,恐惧才真正浮上来。
不是因为饥饿,也不是因为死。
而是因为返航。
有人在黑暗里低声说:
“……如果真要回去怎么办?”
没人回答。
“你觉得,地球上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回来,可能连一口水都找不到。”
“或许,全是横尸。”
“或许空气都不能呼吸。”
“或许那些人就在等我们。”
“那些被留在地表的人……他们会怎么对我们?”
这些话在走廊里一遍遍回荡。
P坐在门后,闭着眼睛。
他想起地球上那片荒凉的盐碱地,想起自己当年在报告里写:
“如果再拖十年,生态将无法逆转。”
可谁都没想过,有一天要带着一船人回去。
带着他们曾经相信的文明,一起回去。
第149天深夜。
I走过空荡的走廊,脚步声在金属壁上回荡,像一声声问句。
他在一面沾着血迹的墙前停下,看见有人用手指蘸血写了四个字:
“我们都错。”
他盯着那行字,胸口缓慢地疼。
不是因为愤怒,也不是因为羞耻。
只是忽然明白:
这艘飞船从没比地球干净多少。
那一夜,星光从舷窗洒进来,冰冷而明亮。
飞船漂在深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再去。
第五章:生命延续
无尽的暗物质漂浮在宇宙深处,像无数细小而冷漠的尘埃。
点点繁星或远或近,各自闪烁着黯淡的光。
这里没有声音,也没有风。
只有亿万年未曾改变的黑。
在这片黑暗里,一艘孤零零的银白色飞船漂浮着。
它没有灯塔,也没有旗帜,只有金属壳上那串字母:
ARK-216
它像一枚曾被寄予希望的胶囊,失去方向地漂在深空。
镜头缓缓拉近,透过外层舷窗,可以看见里面的人。
有人在擦拭地板上的血迹。
他动作一遍遍重复,像一台失去程序的机器。
有女人坐在走廊中央,抱着膝盖,头埋在臂弯里,肩膀轻轻颤抖。
还有一个男人,用空洞的眼神看着舱门,嘴角挂着一点干裂的血痂,像在无声地笑。
远处的走廊里,三个军人背靠着墙坐下,脸色发白,枪横在腿上。
他们手指微微颤抖,却没有再举起来。
更多人把自己锁在狭小的房间里,连呼吸都不敢发出声音。
飞船底层,金属舱壁上,一排淡蓝色符号缓缓闪烁:
自动解锁:第150日
它一直在闪,却没有人注意。
也没能去看。
第150天。
凌晨三点,所有舱室的屏幕忽然亮了。
先是一阵轻微的杂音,像深水里的电流。
然后,一行短短的提示在屏幕中央浮现:
“航行状态解除封锁。”
走廊里没有惊呼。
没有人动。
几秒钟后,有人沙哑地喃喃:
“……解锁是什么意思?”
没人回答。
一阵很轻的脚步声响起。
是I。
他从最内层通道走出来,脸色灰白,眼神空洞。
他缓缓抬起头,看着那行字。
B也走来了。
他看着屏幕,喉咙上下滚动,像是想说什么,却没能发出声音。
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动。
I张了张口,声音低得快要散在空气里:
“……他要返航。”
这句话落下后,有人开始发抖。
“返航?”
“回去?”
“回……哪里?”
他们互相望着,没人敢开口。
P靠在墙上,慢慢闭了闭眼。
有片刻,他以为自己又要呕吐。
回地球。
去降落在那片荒凉的盐碱地,去面对曾经被关在地表、注定死去的所有人。
去看见自己抛弃的一切。
推进器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
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在无声的等待里,有人闭上眼,有人把手指扣进掌心。
他们等着飞船转向。
等着星图上出现那条返航轨迹。
可没有。
所有屏幕一齐亮起。
下一瞬,星图缓缓展开。
一条蓝色的航线,在漆黑的背景上闪了起来:
接近R-7-16星球
刹那间,走廊里响起一阵几乎压抑不住的吸气声。
有人抬起头,脸上带着愕然。
有人用手捂住嘴,眼睛睁得很大。
B微微踉跄一步,像是被这几行字推了一下。
I怔在原地,喉咙里有一声沙哑的嗫嚅:
“……没有返航。”
这时,所有屏幕忽然切换。
A的影像出现了。
他穿着那件灰色的工作服,背景是一间空荡的控制舱,灯光冷白。
他的表情平静,声音轻而清晰:
“如果你们看到这段信息,说明倒计时已经结束。”
没有人再出声。
所有人都盯着那张脸。
“我没有想毁掉你们。”
“从一开始,我就不打算把这艘船变成坟墓。”
I的手慢慢抬起,像要碰一碰屏幕上那个人。
他忽然想起了很多画面:
A在十年前,安静地递过那份修复方案;
A在走廊尽头低下头,什么都没说的背影;
还有他自己,签下那张拒绝批准的报告时,心里那一瞬轻松的快感。
“你们以为返航,是我给你们的终点。”
“你们错了。”
“人类毁掉地球,不等于不配继续活下去。”
“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如果你们连最基本的怜悯都丢掉,就算到了新的星球,也只会把旧的地狱带过去。”
他说话的语气太平静了。
平静得像一份备忘录,而不是遗言。
“飞船的接近程序已经解锁。”
“我已经死了。”
“但如果你们愿意——”
他停顿了一瞬,眼睛似乎在看着每一个人。
“希望你们能比我更相信,人类还配存在。”
画面定格。
他安静看着镜头,目光澄澈。
几秒后,屏幕熄灭。
没人说话。
走廊里很安静,像一口快要干涸的井。
I缓缓垂下手,指尖在空中抖了一下。
他很想开口解释,或辩解,或忏悔。
可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只是觉得胸口很疼。
一种比恐惧更深的东西,慢慢堵住了喉咙。
忽然,有个声音在安静里响起:
“……现在呢?”
声音发涩,像一根快要断掉的线。
没人回答。
很久以后,P走上前去,抬手在操作台上敲了一下。
星图缓缓展开。
那条航线依旧在那里。
目的地:R-7-16星球
没有人再争论。
也没有人投票。
I看着屏幕,慢慢伸出手。
指尖落在那条蓝色的航线最前端。
他呼吸很浅,像怕惊扰什么。
低声说:
“……降下去。”
没人反对。
没有谁发出声音。
所有人都只是站着。
看着那条航线,看着推进器的指示灯一点点亮起。
飞船深处,低沉的轰鸣响起。
金属船体轻轻震动。
航向修正。
他们终于开始接近那颗蔚蓝的星球。
走廊尽头,C蹲下来,抱住自己的孩子。
孩子抬起头,眼神清澈。
“妈妈,我们要去哪儿?”
她没有回答。
只是把他抱得很紧。
飞船在无声的星尘里前行。
没有人知道,那里是不是比地球更好。
也没有人再问,自己配不配得到第二次机会。
飞船冲破了那片蓝绿色的云层时。
第六章:地球
没有人知道,地球在失去最后一座城市后,究竟经历了什么。
也许,海啸退去的地方,留下一片片浅灰色的盐壳,黏稠、干裂,覆盖了曾经的道路与港口。
也许,断裂的山脊在缓缓合拢,新的河道沿着板块缝隙蜿蜒向内陆。
在有些区域,大地依旧沸腾,热浪在残破的地壳下翻滚。
在另一些地方,海水重新吞没低地,潮汐像呼吸一样反复涌入,退去。
从极高的轨道看下去,地球的轮廓依旧完整。
云层在焦褐色的大陆上漂浮,遮住曾经燃烧的城市。
大气层包裹着它,像一条浑浊的、厚重的襁褓。
没有人能分辨,那究竟是腐败,还是新生。
它看上去像一颗在母体里缓慢孕育的胚胎。
没有声音。
没有意识。
只是按照一种不需要证明的规律,继续新陈代谢。
人类消失的地方,植物重新爬上断裂的墙面。
盐碱地里,苔藓在薄薄的潮气里生出微绿的茸毛。
深海里的鲸群继续在冰冷的洋流中缓缓迁徙。
它们没有语言去讨论文明的覆灭。
它们只是沿着祖先的航道,唱着一首从未间断的歌。
有一次,风把一块锈蚀的金属牌掀翻,露出歪歪斜斜的四个字:
“文明纪念”
它在盐壳上停了一夜。
第二天,潮水退去,带走它。
像什么都没有存在过。
地球并不恨人类。
也不怜悯。
它没有愤怒,也没有善意。
它只是活着。
在亿万年的尺度里,任何生灵不过是短暂的寄生虫。
死亡也好,繁盛也好,都会被它消化。
有些人曾经说,地球是母亲。
有些人说,它是审判者。
可它都不是。
它只是一个缓慢成长的婴儿。
它的心跳,是潮汐。
它的呼吸,是地幔深处不知疲倦的热。
它的意志,是无声的时间。
所有生命都曾以为自己至关重要。
其实不过是一阵寄居。
有的虫子死在壳里。
有的虫子飘去别处。
它都不会在意。
它会继续生长,继续收缩,继续修复那些裂开的地表。
等新的生命爬上它的表面,也许会有新的语言。
也许会有新的信仰。
新的傲慢。
新的故事。
可它依旧不会回答。
也不会等待。
它只会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长大。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零重力科幻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0gsf.com/a/17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