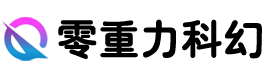故事发生在因全球变暖而混乱的2068年。量子物理学家林砚公布了颠覆性的“量子灵魂扫描仪”研究成果,证实灵魂在死后会随机投胎,并无天堂地狱。为了向权贵证明“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启动了一项秘密实验:追踪刚被处决的独裁者伊莱亚斯·科恩的灵魂。
2068 年的夏天,全球变暖把热浪熬成了一锅粘稠的粥,赤道的气温突破 45℃;北极圈的冰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西泽市的地铁更惨,暴雨把站台灌成了浅滩,而东京银座的机器人服务员,还在机械地鞠躬,自动匹配出观察者的母语,不停地说 “系统故障”。
就在这混乱又荒诞的年份里,林砚站在了日内瓦量子物理实验室的发布会台上。他今年 41 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上的白大褂熨得没有一丝褶皱,左胸别着的 “量子力学教授” 胸牌反射着聚光灯的光,口袋里还塞着本翻得卷边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那是他祖父留下的旧书,书页间夹着泛黄的便签,上面是祖父年轻时的字迹,写着 “伦理是科学的刹车”。
台下坐满了人,全球直播的镜头对准他,屏幕上滚动着 “灵魂研究新突破” 的标题。林砚没说开场白,直接抬手激活了身后的全息投影屏,淡蓝色的数据流瞬间铺满整个墙面,像一片流动的星河。
“没有什么天堂的珍珠门,也没有什么地狱的硫磺火。” 他的声音通过神经扩音器传遍大厅,平淡得像在报天气预报,却让台下瞬间安静下来,“我们团队研发的‘量子灵魂扫描仪’,能捕捉人类死亡后的灵魂量子信号。过去五年,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匿名扫描了超过十亿个样本切片,筛选出三个完整追踪到‘死亡 - 投胎’全流程的案例 —— 为保护家属隐私,所有信息均做了匿名处理,你们看到的只有信号轨迹与核心数据。”
他指尖一点,屏幕上跳出三条猩红的轨迹,像三条挣脱束缚的线,在地球投影上划出不规则的弧线:这是我们首次证实,灵魂与新个体的绑定存在固定精度范围,且投胎落点与地域、种族、阶级毫无关联,纯粹遵循量子随机分布规律。简单说,天堂地狱不存在了,死后的去向,和你闭眼瞎指世界地图的概率差不多。”
屏幕随即切换到三个案例的匿名数据,字体清晰地悬浮在半空,所有可能指向身份的信息都被模糊处理:
案例一:2066 年死亡的中年男性,生前从事高科技行业,灵魂信号在死亡 48 小时后,匹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难民营一名新生儿,SQMA 92.7%;
案例二:2067 年离世的女性教育工作者,在欠发达地区服务超三十年,死后三个月,灵魂信号飘至欧洲发达国家,附着于一个富裕家庭的胎儿体内,SQMA 94.3%;
案例三:2065 年突发疾病去世的普通服务业从业者,灵魂信号意外分裂成双量子态,五个月后分别进入东亚与美洲的两名胎儿体内,二者 SQMA 均为 91.5%。
“投胎窗口期最长半年,和你们玩彩票中头奖的概率本质相同 —— 唯一的区别是,彩票可以不买,投胎没得选。” 林砚补充道,语气里多了几分沉重,“我们公布这些数据,不是为了颠覆信仰,而是想让所有人明白:人类的命运本就紧密相连,今天你所处的阶层、拥有的特权,在下一世荡然无存。”
一位戴金丝眼镜、胸牌写着 “《全球评论》” 的男记者站起来,语气严肃:“林教授,根据您团队发布的《意识量子信号跃迁模型》,灵魂转世的随机性是否会对人类现有伦理体系构成根本性冲击?比如,具有暴力犯罪记录者的灵魂,若转世至普通家庭,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矛盾该如何通过科学或制度层面规避?”
林砚挑了挑眉,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卷边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晃了晃书脊上的烫金字体:“这位先生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问过类似的 ——‘德性是天生的吗’?现在我的答案是,至少从灵魂量子信号来看,不是。那些手上沾过血的人,灵魂信号和普通人没本质区别,就像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 DNA,只是量子排列顺序不同。” 他顿了顿,指尖在全息屏上轻轻划过,调出一组 “灵魂信号特征对比图”,“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通过仪器扫描灵魂的量子切片,但这不代表‘善恶属性’,只代表‘身份唯一性’。至于‘规避矛盾’,目前来看没有完美方案 —— 就像你没法提前预判台风会吹向哪座城市,我们也不可能干预灵魂的随机落点。”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滚油里,全球的反应比预想中更 “理性”,却也更拧巴。梵蒂冈的宗教学者们不再喊 “违背神意”,而是紧急拉着物理学家开线上研讨会,讨论 “量子信号是否属于圣灵的一种形态”,试图给 “不存在的天堂” 找补点面子;联合国伦理委员会加班加点写了篇三万字的报告,一会儿说 “要建立灵魂风险评估体系”,一会儿又说 “不能搞灵魂歧视”,最后连 “是否该给胎儿做灵魂溯源检测” 都没吵出结果;林砚的私人邮箱更惨,三天收到八千多封邮件 —— 一半人骂他 “毁了人类的精神支柱,以后做坏事都没心理负担了”,一半人求他 “帮忙看看我家刚去世的狗,能不能投成富二代家的孩子”,还有个自称 “末日预言家” 的人,发了封附带 Word 文档的邮件,主题栏写着 “警告!邪恶科学家们停止吧!”。
林砚随手打开瞄了眼文档里歪歪扭扭的红色艺术字吸引 “这是外星人的人类控制实验’! 文档末尾还附着两张用绘图工具画 “灵魂绑架示意图“。字歪得像小学生的涂鸦,逻辑也混乱得可笑,林砚盯着屏幕笑了足足五分钟。
混乱持续了一周,直到助手小周抱着一摞泛着金属光泽的全息期刊,走进林砚的办公室。小周的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她手里的资料,全是关于奥西亚共和国前领导人伊莱亚斯科恩的。
这个靠着科技霸权和军事扩张坐稳总统宝座的独裁者,一周前刚在国际法庭的监督下被执行注射死刑。三年前,他突然抛出 “南麓人威胁奥西亚国家安全” 的莫须有罪名,下令对境内及周边的南麓人展开系统性屠杀:无人机对着难民营疯狂轰炸,士兵把南麓人赶进集中营,连老人和婴儿都没放过。半年内,超过四十万南麓人丧命,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人员在废墟里发现尚在襁褓的婴儿尸体时,连见惯了战争灾难的摄影师都忍不住掉泪。可伊莱亚斯却在电视上笑着说 “这是为了奥西亚的种族纯净”,甚至把屠杀视频剪成 “宣传短片”,在全国播放。也正因这份毫无底线的残忍,他成了近百年来首个被全球联合通缉并执行死刑的国家领导人。
“升级后的‘量子灵魂追踪仪’刚调试好,以前我们只能进行切片扫描,而现在终于可以进行主动观测了,第一个案例就选他了。”林砚的指尖悬在悬浮键盘上方,屏幕上还停留着伊莱亚斯处决前的画面。最终,林砚重重按下 “确认” 键。淡蓝色的投影屏幕瞬间炸开一片猩红的数据流,伊莱亚斯的灵魂信号像团躁动的火焰,在全球地图上微弱闪烁 —— 距离他死亡不过 72 小时,距离半年的投胎窗口期,才刚刚开始。
“你还记得我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实验吗?我要的不是‘证明恶有恶报’,是要拿到最直观的数据 —— 证明像科恩这样的独裁者,他的灵魂也会被随机抛入任何命运,可能是难民营的孩子,可能是贫民窟的孤儿。我要把这些数据藏到合适的时机,然后甩到所有权贵面前,让他们看清:人类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今天你漠视的苦难,明天就可能是你下辈子的人生。”林砚说。
小周还想说什么,实验室的警报突然尖啸起来。红色的警示灯在控制台下方微弱闪烁,把林砚和小周的脸照得通红。屏幕上,那团代表伊莱亚斯灵魂的猩红信号不再停留在原地,而是像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开始朝着某个未知方向快速移动 —— 它穿过奥西亚共和国的边境,越过茫茫沙漠,掠过战火纷飞的中东地区,在世界各地间奔走。速度越来越快,屏幕上的坐标不断刷新,却始终无法精准锁定最终目的地。
林砚盯着屏幕上不断跳跃的红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封面。他忽然想起书里的另一句话:“我们重复做的事,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 而现在,一个刚用莫须有罪名终结四十万生命的灵魂,正朝着未知的人群奔去,准备开启新的人生。在灵魂的随机投胎面前,没有谁能永远站在苦难之外。
林砚盯着实验室屏幕上那团猩红的光点时,窗外西泽市的暴雨正砸在玻璃上,像无数根细针要刺破这层薄薄的屏障。距离伊莱亚斯科恩被处决已过去一个月,这团代表独裁者灵魂的信号,前几天还在全球地图上漫无目的地飘,像只找不着方向的飞蛾 —— 有时掠过北欧的雪原,有时停在南美雨林上空,SQMA 数值始终在 “未匹配” 的波动区间里徘徊。可从昨天凌晨开始,它突然有了明确的轨迹,一路朝着南麓的方向疾行。
“教授,信号稳定度已经连续 18 小时维持在 92%,从来没见过随机漂移的信号这么‘执着’。” 小周的声音从脑机里传来,带着抑制不住的紧张,她的指尖在操控屏上飞快滑动,最后锁定在哈兰医院上。三维模型瞬间铺满实验室的全息投影,“哈兰是南麓族聚居地,三个月前刚扩建了妇幼科室,现在有十七个孕妇在待产,其中一个叫法蒂玛的南麓族孕妇,预产期就在今天,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要生了。”
林砚的指节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他的目光顺着人工智能调取的孕妇档案往下扫,当 “法蒂玛” 三个字与身世简介同时出现时,一些来自AI搜索的内容撞进脑海,科恩下令轰炸南麓族村庄那天,法蒂玛的父母把她塞进地窖缝隙,自己却被炸弹碎片击中,救援人员找到他们时,两人的手还保持着护住地窖的姿势。
现在,那个毁掉她家庭的独裁者的灵魂,正朝着她即将出生的孩子奔去。
“已经提前通知医院了,说有科学家要去” 小周说道。“流程很快就走好了。”
林砚的指尖点在屏幕上,红色轨迹在地球模型上划出一道决绝的弧线,从奥西亚边境直插哈兰,没有丝毫偏差,“难道这份独裁者灵魂要成为受害者后代’?” 话出口时,他心底竟掠过一丝难以言说的欣喜 —— 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将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震撼的实证:曾经高高在上的独裁者,灵魂竟要托生在被他迫害的家庭,这比任何数据都更能撕碎 “特权永恒” 的假象。他抓起桌上的便携式量子观测仪 —— 外壳被伪装成普通胎儿心率监测仪,塞进白大褂口袋,“我现在去哈兰医院,你留在实验室盯着信号,每十分钟同步一次数据,这可能是我们实验最关键的时刻。”
量子真空穿梭机在专用轨道上疾驰,窗外的雨雾渐渐变成中东的荒漠。林砚倚着舷窗,双眼紧闭,意识深处却翻涌着两段画面:一段是科恩在奥西亚电视台的演讲,他穿着军装做出伪君子的笑容,宣称 “南麓人是国家毒瘤”,身后村庄正被炮火吞噬;另一段是上周法蒂玛在绿洲社交平台发布的全息动态 —— 她坐在病床上,举着父母的旧照片,阳光透过纱帘洒在她脸上,语气平静又温柔:“战争已经结束了,而爱能化解伤痛。”
AI 情感识别系统标记的 “眼瞳高光数值”,此刻正与量子追踪仪的猩红信号交织。林砚忽然觉得,这或许是命运最辛辣的安排:让双手沾满鲜血的独裁者,在新生命里感受受害者家庭的温度 —— 这将是他向权贵证明 “命运共同体” 的最好证据,比任何报告都更有冲击力。
穿梭机降落在哈兰医院门口时,雨已经停了。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与沙枣花混合的味道,远处传来朗朗的诵经声。
他在走廊拐角停下脚步,透过病房门缝看去:法蒂玛坐在病床上,背靠软枕,一只手轻轻放在隆起的肚子上,另一只手拿着彩色绘本,小声念着故事。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她身上镀上暖金色光晕,像一道温柔的屏障,将所有阴霾隔绝在外。
林砚的脚步突然顿住,心底的欣喜却瞬间被不安取代。口袋里的观测仪轻轻震动,屏幕上跳出猩红小字:“目标胎儿匹配倒计时:48 分钟”。他想起自己在发布会上说的 “灵魂随机如闭眼指地图”,可此刻,“随机” 带来的不是公平,而是残忍 —— 法蒂玛在仇恨里长大,却选择用爱面对世界,她期待的孩子,竟可能承载着毁掉她家庭的灵魂。
“请问是林砚教授吗?” 一段淡蓝色全息文字在视网膜边缘闪烁,护士阿米拉的声音被脑机自动翻译完之后带着电子合成尾调,“法蒂玛女士刚才还问,是不是有科学家来给宝宝做健康检测。”
病房里的歌声停了,法蒂玛转过头,看到林砚时立刻露出笑容,挥手打招呼:“科学家医生,您来啦!我们真幸运,听说您是国际组织无偿来我们这儿检测新生儿健康的吧”
她的眼神里满是期待,林砚的喉咙却像被堵住。口袋里的观测仪又震了一下,他悄悄按亮屏幕 —— 猩红信号已与胎儿生命信号出现微弱重叠,SQMA 数值显示 “35%”,且每分钟都在攀升。他张了张嘴,想说的话卡在喉咙里,最后只挤出一句干巴巴的:“我…… 先帮你做个基础检测。”
他走到病床边,将观测仪探头轻轻贴在法蒂玛的肚子上。视网膜上瞬间浮现数据流:胎儿心跳平稳有力,而那团猩红信号像潮水般漫过心跳曲线,重合度数值不断跳动 ——36%,37%,38%…… 林砚强装镇定地说:“宝宝很健康,心率和胎动都正常。” 可指尖却控制不住地发凉,心底的不安像潮水般蔓延:他要的是 “命运共同体” 的实证,眼前这有如戏剧一般的剧情走向,这将是一份最好的实证,可这份实证,要建立在一个女孩的痛苦之上吗?
“我还有点事要和院长沟通,等会儿再过来。” 他几乎是逃一般地走出病房,在走廊尽头的楼梯间停下,太阳穴处的脑机芯片泛起蓝光,他压低声音发送加密讯息:“信号重合度已到 40%,仪器参数没问题吧?这可能是实验最关键的证据。”
三秒后,小周的回复浮现在视野右下角:“参数反复核对过三次,都正常,C-73 投胎到法蒂玛胎儿的概率已超 99.9%。”
林砚关闭通讯,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那本《尼各马可伦理学》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扉页的 “恶的本质是选择” 被灯光照得格外清晰。他弯腰去捡,手指碰到书里的金属书签,冰凉的触感让他瞬间清醒:他期待的 “实证”,本质上是将法蒂玛推向深渊。如果不告诉她真相,她会带着对孩子的期待,抚养一个承载着独裁者灵魂的生命;可如果告诉她,又会彻底打碎她的希望,让她重新陷入仇恨的泥沼。
病房里,法蒂玛又唱起了摇篮曲,温柔的调子像一根细针,扎在林砚心上。
林砚在楼梯间站了足足十分钟,观测仪上猩红信号与胎儿心跳的重合度从 40% 爬至 50%,每跳一个百分点,太阳穴的脑机接口就传来一阵刺痛 —— 团队的讯息像潮水般涌来:“保密协议不能破,我们只是观测者!”“数据外泄会终止整个实验!”“别忘了初衷是警示权贵,不是毁了普通家庭!”
他攥着《尼各马可伦理学》,书页磨损的边缘硌着掌心,祖父 “伦理是科学的刹车” 的字迹在脑海里盘旋。走廊感应灯随脚步明灭,光影晃得他眼晕,心里两个念头反复拉扯:守住数据,还是守住法蒂玛的期待?最终,他深吸一口气,把观测仪调成 “普通心率监测” 模式,转身走向病房。
推开门时,法蒂玛刚喝完营养液,指尖贴着肚子轻声说:“等爸爸从难民营回来,我们去看沙枣林好不好?” 见林砚进来,她眼里亮起来:“林教授,您是研究‘意识量子信号’的吧?我刷到过报道,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灵魂呀?”
林砚的动作顿了一下。他原本准备用 “量子信号匹配”“生命频率重合” 这些专业术语绕开 “灵魂” 这个敏感词。可他没料到,在信息透明化的时代,配合 AI 与脑机接口催生的极速学习模式,连法蒂玛这样没有科研背景的普通人,都能迅速理解前沿理论,还主动戳破了这层窗户纸。“很多人在屠杀中去世了,但是活下来的人都说希望亲人转世能投好胎。” 法蒂玛摸着肚子笑,语气轻得像羽毛,可林砚通过脑机捕捉到她神经电流的细微震颤 —— 那是提到 “屠杀” 时的恐惧应激,藏在温柔下,不易察觉。
林砚喉结动了动,口袋里的观测仪硌得慌。他掏出仪器,假装调试:“我帮宝宝做个基础监测,看看心率。” 探头贴上法蒂玛的肚子,视网膜上瞬间浮现数据流:猩红信号正像潮水漫过蓝色心跳曲线,重合度已达 45%,且毫无波动,和普通灵魂信号的自然起伏截然不同。
“宝宝很健康,心率很稳。” 他强装镇定收起仪器。
“那就好。” 法蒂玛松了口气,又哼起南麓族摇篮曲,阳光落在她脸上,像层温柔的屏障。林砚看着她的笑容,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明明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承载着屠杀她父母的人的灵魂,却不能说。
“我还要和院长对接点事,先不打扰你了。” 他几乎是逃一般地起身,走到门口时,法蒂玛突然说:“教授,谢谢你。我希望宝宝以后也能像你一样,用知识帮别人。”
林砚脚步顿住,没回头,只含糊应了声 “会的”。走出病房,他靠在墙上,摸出《尼各马可伦理学》,扉页 “恶的本质是选择” 的字迹刺得眼疼。他掏出钢笔,想写点什么,笔尖悬了半天,只在空白处画了个凌乱的圈 —— 他选择了守密,却把伦理的枷锁,牢牢锁在了自己心上。
脑机里团队的讯息还在闪烁,可林砚只觉得疲惫。他看着观测仪上 48% 的重合度,轻声呢喃:“对不起,法蒂玛。”
哈兰医院的新生儿监护室里,恒温系统将温度稳定在 25℃,柔和的白光透过特制玻璃洒在婴儿床前,便携式量子观测仪的屏幕亮着淡蓝色的光,上面的数字 ——96.4%,像一颗被精心打磨的宝石,吸引着团队所有人的目光。
“96.4%!教授,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SQMA 数值!” 团队里最年轻的研究员小李举着全息数据报告,声音里满是抑制不住的兴奋,“之前最高的案例也才 94.3%,诺亚这个样本,简直是‘灵魂匹配稳定性’的完美范本!”
林砚站在监护室外,指尖轻轻抵着玻璃,看着里面熟睡的诺亚
“通知实验室,把诺亚的观测数据列为最高优先级,每天进行一次量子深度扫描,记录 SQMA 的波动情况。” 林砚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我们要完整记录这个‘超稳定样本’的成长轨迹,这会是‘命运共同体实证实验’最有力的证据 —— 连独裁者的灵魂,都能与受害者家庭的新生命达成高度匹配,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命运无特权’?”
诺亚出生一周后,法蒂玛抱着他回了家 —— 窗外是沙枣林,阳光落在婴儿床纱帘上,暖得像裹了层绒。没人知道,团队早借 “社区改造” 名义,在屋里布了观测网:空气净化器藏着信号接收器,温湿度传感器嵌着扫描芯片,这一切经政府许可,隐蔽得没惊动任何人,只有对面 “便民服务站” 里,小周盯着数据流,指尖偶尔发颤。
“命运共同体实验” 第一阶段已收尾:SQMA 从出生 96.4% 稳涨到 6 个月 97.1%,证实诺亚是科恩转世。现在可以算是补充实验,计划跟踪至 5 岁,验证灵魂是否脱轨、善恶是否随投胎延续等。
诺亚满一岁那天,哈兰郊区的沙枣林开了第一朵花,正如几千年来的每一个哈兰春天一样。
“教授,您能来一下吗?有件事…… 我觉得必须跟您说。” 小周的声音压得很低,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投影仪的光映在她脸上,显得格外凝重。
林砚心里咯噔一下,跟着小周走进隔壁的临时办公室。小周按下投影仪开关,墙上立刻浮现出两条对比鲜明的曲线:一条是之前团收集127 个样本切片的 SQMA 值,像起伏的波浪,在 90%-95% 区间内上下浮动;另一条是诺亚的曲线,从出生时的 96.4% 开始,呈一条近乎完美的直线,缓慢却坚定地向上攀升,终点直指 100%。
“这是我用以前所有样本切片建立的‘SQMA 自然波动模型’。” 小周的声音发颤,她指着诺亚的曲线,指尖微微颤抖,“所有样本的 SQMA都在之间,只有诺亚的…… 是严格线性增长。按这个趋势计算,他的 SQMA 会在 3 岁时达到 100%。”
“100% 又怎么样?” 林砚的心跳开始加速,却还在试图维持镇定,“我们之前不是说过,SQMA 越高,灵魂绑定越稳定吗?”
“您忘了我们最初对 100% 的定义了吗?” 小周猛地抬头,眼里满是惊恐,“您在发布会上说过,SQMA 是‘灵魂与新个体的匹配精度’,100% 意味着 —— 灵魂与新个体完全重合,不是转世,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3 岁的诺亚,会变成第二个伊莱亚斯科恩!”
“轰” 的一声,林砚感觉大脑像被炸开,背后瞬间渗出冷汗。
“不可能…… 这只是模型预测,说不定哪里出错了。” 林砚的声音有些沙哑,他伸手想去关掉投影仪,却被小周拦住。
“教授,我核对了三遍数据,没有错!” 小周的声音带着哭腔,“这根本不是自然现象!”
办公室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林砚看着墙上那条直指 100% 的红色曲线,又想起法蒂玛抱着诺亚时温柔的笑容,心里像被撕裂成两半 —— 一边是坚持了多年的科研理想,一边是一个孩子的未来。
最终,他深吸一口气,冷静似乎重新占据了他的大脑,说到: “加倍观测的频率吧,如果超过阈值,立刻停止试验。”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一击。没人知道为什么,诺亚的 SQMA增长速度加快了,林砚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观测仪上 97.8% 的数值,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无力。窗外的沙枣花随风飘落,落在观测仪的屏幕上,遮住了那条刺眼的红色曲线,却遮不住他心里越来越深的恐惧 —— 他好像亲手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现在,却找不到关上它的方法。
哈兰的雨季来得突然,连续半个月的阴雨让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林砚坐在临时办公室里,观测仪屏幕上的数字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他的神经 ——99.2%。这个数值比上周又涨了 0.3%,而诺亚的异常行为,也开始朝着更可怕的方向发展。
那天清晨,诺亚冲在纸上用蜡笔歪歪扭扭地画着一个图案—— 那是奥西亚军徽的简化版,和科恩军装领口的标志一模一样。有时法蒂玛放南麓族的歌谣,诺亚突然把收音机摔了。
昨天电视里播奥西亚的新闻,他居然停下来,学着里面的人敬礼。
有次,林砚找了个机会去法蒂玛家,看着诺亚的眼睛。孩子的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清澈,反而多了一丝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冷漠。
那天之后,林砚彻底陷入了抑郁。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白天盯着观测仪上的红色曲线发呆,夜晚就翻出祖父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伦理是科学的刹车” 那行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他开始反复回想自己做这个实验的初衷 —— 明明是想证明 “命运无特权”,警示权贵善待他人,可现在,却无意中见证了一个无辜的孩子推向了 “成为恶魔” 的深渊。
转折发生在一次午休。林砚躺在简易床上,用记忆检索仪回溯着大学时的量子物理教材,试图用公式麻痹自己。当翻到 “薛定谔的猫” 那一章,书上的一句话突然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混沌的思绪:“观测行为本身,会导致量子叠加态坍缩,使原本可能存在的多种状态,变为唯一的确定状态。”
林砚猛地抬起头,目光落在观测仪上。诺亚的 SQMA 从出生时的 96.4% 线性增长到 99.2%,而加强观测了之后,增长也加倍了。这哪里是 “灵魂绑定稳定”,分明是他们的观测,在不断强化科恩灵魂与诺亚的绑定,让 “可能脱离的叠加态”,一步步坍缩成 “完全重合的固定态”!
他疯了一样冲向电脑,想找出那个末日预言家的邮件。可当他打开邮箱,看到的只有系统提示:“30 天前的垃圾邮件已自动清理,无法恢复。” 林砚瘫坐在椅子上,冷汗浸湿了衬衫,后背的衣服贴在皮肤上,冰凉刺骨。他想起“预言家”画的丑陋的示意图,想起诺亚画的军徽,此刻都串联成一条清晰的线,指向那个让他不寒而栗的真相:是他们的观测,在把诺亚变成科恩。
“必须停下…… 一定要停下……” 林砚喃喃自语,他看着屏幕上 99.93% 的数值,深吸一口气。他从口袋里掏出《尼各马可伦理学》,翻到最后一页,写下一行字:“科学的意义,是守护生命,而非创造灾难。” 然后把书放在桌上,转身走向主控台。
林砚双手死死按住 “紧急关机” 按钮 —— 红色的警报声瞬间响彻实验室,所有观测软件同时关闭,屏幕瞬间变黑,只有主控台的应急灯还在闪烁,映着林砚决绝的脸。
很多年之后,林砚再次来到哈兰参加国际会议。
一阵风吹过,沙枣花落在林砚的肩上。他抬头望向天空,回想起这段无法遗忘的试验,身体却突然像被重锤击中般一震 —— 手指间的沙枣 “啪嗒” 掉在地上,一个念头像闪电般钻进他的脑海,再也无法剥离。
他想起末日预言家丑陋的图示,想起诺亚的 SQMA 和科研观测分毫不差的线性增长,想起科恩的灵魂为什么偏偏投到法蒂玛的孩子身上。
林砚缓缓抬起头,目光越过沙枣林,望向深邃的宇宙。天空是纯粹的蓝色,没有一丝云彩,却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嘴唇哆嗦着,声音轻得像叹息,又像是在和某个看不见的存在对话:“原来是这样啊…… 我们的观测、诺亚的异常、甚至科恩的投胎…… 都是设定好的吧?”
风突然停了,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诺亚的笑声仿佛从远处传来,却显得格外遥远。
他不知道这个疑问有没有答案,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也在 “设定” 之中。
阳光再次洒在林砚的脸上,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朝着法蒂玛和诺亚的家的方向走去。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疑问,但此刻,他只想好好看着这个特殊的孩子,感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零重力科幻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0gsf.com/a/18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