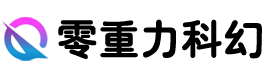我这票,投得像个笑话。
联合国大会会场,气氛凝重。巨大的环形会场,表决器亮起一片刺眼的红。削减太空探索预算,以绝对优势通过。除了我和那几个孤零零的绿色“反对”,微小的绿点眨眼就淹没在猩红里。
“太贵了!”散会后,走廊里的议论嗡嗡作响,“登陆那个破石头月亮就要几千亿?够修多少路,盖多少学校?光速飞船?做梦吧!”一个大腹便便的代表对着镜头挥舞手指。
另一个人接口,语气懒散:“就是。太空?元宇宙里,星辰大海触手可及。费那劲干嘛?”
我快步穿过嘈杂。他们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想懂。
人类把自己关在摇篮里,还得意洋洋地装饰栏杆。一次像样的太阳耀斑,一场小行星雨,地球打个喷嚏——这点靠虚拟幻象和地表基建堆砌的“文明”,就会像沙滩城堡,被一个浪头抹平。没有踏出母星的种族,在星辰尺度上,算不上文明。原始,脆弱。
可我能做什么?一个夹在大国缝隙里、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小国元首。我的反对票,轻如尘埃。
可我不甘心啊。
回酒店路上,车载新闻里女主播声音带着一丝甜腻:“…元宇宙社区‘星海彼岸’今日用户突破三十亿…”
窗外摩天楼的光污染染红了夜空,不见星光,我听着烦,一把关了广播。
司机从后视镜瞄着我:“总统先生,回酒店?”
“嗯” 沉默片刻,我又问“你说,还有谁……还在往天上使劲儿看?哪怕一点点?” 我的声音很干。
他挠了挠头,动作带着点拉美人特有的随意。“这个……可能……中国?”他不太确定地说,“他们那个‘天宫’空间站,好像还在往上加模块?新闻提过一嘴,不多。”
中国?我脑子里一动。
行程表是早就排满的。几天后,我坐在一辆平稳行驶的黑色礼宾轿车里,窗外是北京宽阔得有点空旷的街道和高耸入云的建筑森林。目的地是人民大会堂某个侧厅。
接见我的是位温文儒雅的总理。办公室很大,透着一种沉静的秩序感。墙上挂着大幅水墨山水,烟云缭绕。寒暄,落座,上茶。青瓷茶杯里飘着几片嫩绿的叶子,热气袅袅。我努力组织着中文词汇,尽量去掉那点该死的西语腔调,把我的忧虑,我那点被联合国踩进泥里的“反对票”,还有那想法——人类必须走出去,必须重新抬头看星星——一股脑倒了出来。
总理安静地听着,脸上专注。 直到我提到"重启太空探索",他端茶杯的手顿了一下,放下。
“?梅希亚总统,”他开口,声音平缓,但眼神锐利地闪了一下,“您的想法……很有远见,也很有勇气。这让我想起我们一句古话,‘位卑未敢忘忧国’。”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不过,这件事……涉及面太广了。或许,您应该和我们主席深入谈谈。”
主席?!我端着茶杯的手指一紧。心跳猛然开始加快。
就是这么措不及防下,我准备去面见主席了。
车子驶过长安街,天安门城楼的轮廓在深秋清冽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庄重。我看着天安门心跳逐渐加快,头顶冒汗。我下意识地用手擦了擦。卡洛斯坐在副驾,透过后视镜瞄了我一眼,眼神里全是“老大你稳住”的无声呐喊。
会见的地方在一间更小的厅。厚重的木门无声滑开。他就在那里,站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有种沉静的厚重感。
主席身穿深色的中山装,熨帖得一丝不苟。
握手。他的手掌宽厚,干燥,有力。我努力抑制住指尖那点轻微的颤抖。
“?梅希亚总统,”他开口,声音不高,带着点淡淡的京腔,却清晰地送入耳中,“总理跟我简单提过了。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没有寒暄,没有扯皮,我深吸一口气,将在联合国憋回的话,连同烧灼心肺的焦虑,倒了出来。 人类的短视,文明的脆弱......说到激动处,我的中文词穷,手势在空中徒劳地比划了一下,像个笨拙的哑剧演员。
“所以,”我盯着他沉静如深潭的眼睛,像抓住最后一根浮木,“萨尔瓦多愿意倾尽全力,但我们需要伙伴!需要像中国这样……还在仰望星空的伙伴!我们能不能……一起做点什么?哪怕只是点一把火,让人类重新看看头顶?”
声音带上了一丝恳求。
他一直没有打断我,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端起手边的白瓷茶杯,抿上一小口。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我略显急促的声音,以及钟表的"咔哒"声。
等我说完,最后一点声音消失在空旷里。他放下茶杯,杯底碰触红木桌面,发出极轻微的一声“嗒”。
沉默。
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太阳穴的突突声。
他抬起眼,目光落在我脸上,那眼神像是穿透了此刻的焦虑,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梅希亚总统,”他终于开口,声音依旧平缓,却让我兴奋,“你的忧虑,我懂。人类的目光,不该只盯着脚下的泥泞。”
他顿了顿,手指轻叩桌面。"但现实是,两百多个国家,两百多种声音。两个国家的意志,"他轻轻摇头,嘴角扯出一丝苦笑,“难。”
我那点希望,瞬间熄灭。再然后,主席和我谈话的声音成了嗡嗡的背景。我像个泄气的皮球,告辞出来。
北京的晚风凉,吹在脸上。回酒店?不甘心。
我必须为了人类找到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的的,实际的办法,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来都来了,不能空手而归,据说中国有许多古籍,记载着珍贵的的知识和思想。这段时间我也自学了中文,于是乎,我决定找中国的书去读一读。但愿我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书店,” 我对司机说,“最大的,能挖出老古董的那种。”
司机还是很靠谱的,他把我拉到了琉璃厂。空气里有旧纸和墨汁味。我在泛黄的书堆里刨了几天,眼睛发花。《孙子》的“诡道”,《天工开物》的机关,《庄子》的“徙于南冥”……我没有管,一股脑买了过来。
回去后,我立马把这几本书翻得头晕,有收获吗?有。可要说对现在人类现状有帮助吗?…我不知道
烦躁在疯长。我的目光扫过角落书桌上一本摊开的硬壳书,不知什么时候放上去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文版,封面上画着云雾缭绕的仙山和驾鹤的仙人。
鬼使神差地,我走过去,重重地坐下,把那本厚厚的书拖到面前。手指烦躁地划过目录页。精卫填海?女娲补天?不,太悲壮了。翻过一页。愚公移山?太慢。再翻……手指停住了。
徐福东渡·三神山
一段尘封在故纸堆里的旧事。两千多年前,一个叫嬴政的帝王,横扫六合,坐拥天下。他怕死,怕得要命。于是有个叫徐福的方士跳出来,说东海之外,有三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山上有神仙,神仙手里有长生不死药。只要给他人、给船、给钱,他就能把仙药带回来。
那个千古一帝,信了。倾举国之力,造巨船,遣童男童女数千人,由徐福带着,浩浩荡荡驶向茫茫大海,寻找虚无缥缈的仙山和不死药。
仙药?当然屁都没找到。徐福和他那支庞大的船队,消失在海天尽头,成了历史的一个谜团、乃至一个笑话。
可那支船队,那些为了一个谎言而建造的、当时最庞大最先进的船只……它们劈波斩浪,真的驶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它们绘制了最初的远海航线,积累了最初的天文导航知识,甚至可能……意外地触碰到了某些未知陆地的边缘!
一个念头猛地撞进脑海:
长生药!一个虚无缥缈的“利”!就足以驱动一个帝王,举倾国之力,把目光投向未知的海洋!
那……如果是“外星来信”呢?一个足以让全人类疯狂、让所有国家放下争端、争先恐后冲向星海的“外星大礼包”呢?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近乎灼烧的兴奋。我一把抓起书桌上酒店提供的便签纸和笔,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杆,潦草地写下几个关键词:木星!信号!礼物!无法破解!外星!
笔尖差点戳破薄薄的纸张。
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擂动,血液冲上头顶,指尖因为兴奋而微微发麻。我猛地站起身,膝盖撞到了沉重的红木桌角,钻心地疼,但这疼痛反而让我更加清醒。顾不上跟一脸愕然的助手详细解释,我胡乱收拾起自己的东西,语无伦次地又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几乎是踉跄着冲出了那充满书香的幽静殿堂。阳光刺眼,外面车水马龙,喧嚣扑面而来,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必须再去一次北京!立刻!马上!
这一次,踏入那个充满茶香和沉静力量的房间,我几乎是扑到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前。胸膛剧烈起伏,一路疾驰带来的燥热还未散去,我顾不上平复呼吸,双手撑在冰凉的桌面上,目光灼灼地盯着办公桌后那个身影。
“主席先生!蓬莱!”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嘶哑,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秦始皇的蓬莱仙山!长生药是假的,但投入是真的,结果呢?航海技术大发展!我们需要的不是说服,是诱惑!一个让全人类无法抗拒,必须拼尽全力去追逐的‘太空仙山’!一个……一个来自星海彼岸的‘邀请函’!”
我把那个在古籍幽香和茶水意外中诞生的疯狂构想和盘托出。房间里只剩下我急促的呼吸声。说完,我像耗尽了所有力气,微微喘息着,等待着最终的裁决。是斥责我异想天开?还是……
他沉默了。比上次更久。目光低垂,手指无意识摩挲文件边缘。
然后就是死一样的安静。
我后背冷汗瞬间浸透,冰凉。完了?太莽撞了?像个疯子?就在我懊悔不已时,对面却传来一声极轻、极缓的吐气。接着,是指关节叩击硬木桌面的声音——笃,笃,笃。每一下都敲在我紧绷的神经上。
“?梅希亚总统,” 主席的声音终于响起,低沉,“此计…险呐。” 他又停顿了,那停顿漫长而难熬,“不过…存亡之际,行奇谋,倒也在理。以利驱之…” 他斟酌着字眼,声音透出疲惫,“…确是人类本性。放手去做吧。”
“?梅希亚总统,你成功带来了一把钥匙……虽然它是欺骗铸成的。”
三天。我在钓鱼台国宾馆那间能望见西山的大套房里,像头困兽一样转悠了整整三天。茶喝不出味儿,饭嚼不出香,觉睡得稀碎。直到傍晚,保密专线响了。
“成了。” 电话那头就两个字。
再见到主席,是在一个我完全认不出模样的地方。深埋地下,墙壁是厚重的银灰色合金,空气里有股冰冷的、机器特有的金属和臭氧混合的味道。巨大屏幕上,幽蓝深邃的宇宙背景前,一颗色彩斑斓的巨行星缓缓旋转——木星。它旁边,一个不起眼的金属小点正被标注着复杂的轨道参数。
“它叫‘愚公’。” 主席指着那个小点。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底深处,有种压着千钧重担的亮光。
“我们将在月球发射它,三天后出发。抵达木星轨道后,它会向地球定向发送一段特殊信号。”
“至于会不会被发现,”主席顿了顿,“我们赌的是,当“外星信号”这个惊天消息出现时,人类的震惊、渴望,会淹没对最初那个“不起眼”探测器和其关联的细致追查。”
他转向旁边一位花白头发的科学家花白头发的科学家,“李院士,给?梅希亚总统讲讲。”
李院士兴奋的推了推眼镜:“信号本身是段图像信息以及文字信息,用我们最新搞出来的‘量子混沌加密’打包,基于量子纠缠态和木星大气层特定湍流模式的物理特性混合编译。简单说,它发回来,地球上所有大功率射电望远镜都能‘听’到这段‘噪音’,但只有我们能按特定算法,把它‘翻译’成图片和文字。” 他语速很快,带着科研人员特有的亢奋,“图像内容嘛…” 他搓了搓手,看向主席。
主席颔了颔首。李院士敲下键盘。副屏亮起:木星大红斑下,悬浮着几样东西------一个结构精巧绝伦的环形装置,一株在真空中盛放、散发光晕的奇异植物,一块刻满无法解读信息的晶体。
图像的底部,用某种简洁、优雅、绝非人类已知任何文字体系的符号,传达着一个清晰得令人头皮发麻的意思:
【礼物已备。木星静候。期待相逢。】
他停顿,目光扫过我震惊的脸:"'信使'播发信号后,利用加尼米德冰下地质活动和木星环境......进行不可逆物理销毁。不留痕迹。"
"文字信号内容..."我的声音干涩。
李院士翻过一页文件,上面是复杂波形图。"内容是多重加密伪装的数学序列、几何图形及一段'问候'脉冲。关键,"他眼神锐利,"全球主要天文台将在'望舒'发现木卫三异常能量后,'恰好'接收到。经过预设的'艰难'破译------破译密钥会适时'泄露'------全球将'解读'出统一信息核心:一个自称'观测者'的未知文明,在木星系为人类留下了'技术礼物'。期待人类获取它,并加入星辰交流。"
房间里死一般寂静。茶香依旧,却闻出了硝烟的味道。伪造外星信号,利用木星系统的险境作为掩护和毁灭场,引导全人类进行一场“破译”与“寻宝”……这计划的冷酷精密,让我脊背发凉。
办公桌后,他靠向椅背,双手交叉,目光如同深潭,望向我,也仿佛望向未来。
“?梅希亚总统,”主席的声音低沉凝重,“‘星槎’已备。这艘谎言驱动的船,一旦启航,没有回头路。虽然我们会尽力控制以后的舆论,可…人类是获得星海的翅膀,还是坠入更深的黑暗……无人能料。你确定要按下发射钮?”
时间凝固。我想起联合国会场的猩红,古籍里的仙山。绝望与希望,谎言与生存。
我抬起头,迎上目光。喉咙发紧,声音清晰,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然:
“确定。”
三年后,深夜。
萨尔瓦多国家天文台深处,绝对屏蔽监测室。
空气里是机器低沉的嗡鸣和冷却液的金属气味。巨大的主屏幕上,一片代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细密跳动的灰白色噪点。角落里,几个穿深蓝色工装的技术员盯着分屏,手指偶尔敲击键盘。平静。
我坐在角落的硬椅上,背挺直,双手紧握。卡洛斯在旁边,身体前倾,死死盯着主屏幕。他手里捏着个半空的塑料水瓶,瓶身被无意识地捏紧。
时间爬行。主屏幕上的噪点依旧毫无规律地跳跃。
突然!
“滴滴滴——!”
一阵尖锐、急促、完全非系统常规的警报声撕裂了监测室的平静!
所有技术员猛地从座位上站起!
惊呼炸开。主屏幕上,那片灰白噪点中心,毫无征兆地爆开一团剧烈波动的无颜色信号!那信号刺眼,像宇宙黑暗幕布上睁开的一只冰冷巨眼!
信号强度读数疯涨,瞬间突破所有预设阈值红线,发出连绵不绝的刺耳蜂鸣!频谱分析窗口里,平滑基线被彻底撕裂,代之以一团狂暴扭曲、不断变幻形态的能量尖峰,其模式完全超出任何已知自然现象或人类造物的范畴!
“上帝啊……”一个年轻技术员失神喃喃,记录板掉在地上。
“快!最高优先级记录!所有通道!备份!立刻备份!”监测主管的嗓子喊劈了,脸上血色褪尽,只剩下惊恐与职业狂热。
整个监测室彻底炸了锅。键盘被敲得如同暴雨,通话器里传来语无伦次的吼叫,椅子被慌乱的动作带倒,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人们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又被那屏幕上妖异的紫光死死钉住视线。
我僵在椅子上,全身的血液似乎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成冰坨。耳朵里嗡嗡作响,那尖锐的警报声、疯狂的蜂鸣、失控的呼喊……都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变得模糊而遥远。只有主屏幕上那团剧烈搏动、仿佛拥有生命的无颜色信号,无比清晰,无比巨大,带着一种非人的、冰冷的意志,蛮横地撞入我的视野,占据了我整个大脑。
成了。
这两个字猛地烙进我的意识深处。没有预想中的狂喜,没有巨大的兴奋,只有一种……近乎虚脱的眩晕感,和一股从骨髓深处渗出来的、冰寒彻骨的战栗。我放在膝盖上的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
卡洛斯手里的矿泉水瓶终于彻底报废,在他无意识的巨力下“咔嚓”一声被捏扁,浑浊的水流了一地。他浑然不觉,只是死死地、死死地盯着屏幕,眼球因为过度用力而布满血丝,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意义不明的抽气声。
无颜色的信号还在屏幕上狂暴地闪烁,像一只来自宇宙深渊的、充满嘲讽和诱惑的冰冷眼眸,无声地俯视着监测室里这群陷入彻底混乱、渺小如尘埃的人类。
它来了。
又几年后,我再次受邀访问中国。还是那间深埋地下的指挥中心。巨大的主屏幕被分割成无数块。一块显示着地球轨道上密密麻麻、如同炸了窝马蜂般的新发射物追踪标识。一块是木星轨道,几个代表不同国家最新探测器的光点,正小心翼翼地绕着那颗气态巨行星打转。最大的一块屏幕中央,是木卫三——那颗被设定为“信号源”的冰卫星。高清镜头扫过去,全是裂开的冰壳,灰扑扑一片,死气沉沉,连个影子都没有。
主席站在屏幕前,背影依旧挺直。我走过去,和他并肩站着。屏幕上,一个代表欧空局着陆器的图标,正缓缓降落在木卫三一处预设的“可疑”冰裂谷边缘。
“都在找啊,” 我低声说,嗓子有点紧,“掘地三尺。”
“嗯。” 主席应了一声,目光锐利锁定实时画面。冰尘在着陆喷焰下四散飞扬,高清镜头缓缓扫过亘古死寂的冰原,除了嶙峋的冰岩和深邃的裂缝,什么都没有。绝对的,令人窒息的荒芜。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指挥中心里静得可怕,只有仪器运行低沉的嗡鸣,还有偶尔响起的、几乎听不见的坐标报告声。各国探测器的图标在屏幕上徒劳地移动、扫描、钻探。每一次数据传输完毕,带来的都是更深的失望。
屏幕上,代表“愚公”最后自毁坐标的那个小点,孤零零地悬在木星轨道深处,像一个早已熄灭、无人再记得的微小句号。
我的心情在信号的一次次传递里越来越紧张,手心冰凉。成功了?失败了?那点火星子,是把人类重新推向星空,还是…彻底暴露了我们这个蹩脚骗局?
全世界最顶尖的眼睛都盯着木星,每分每秒都是走钢丝!那个精心炮制的“木卫三冰层深处”的诱饵,能撑多久?
或许这已经不重要了,我相信,在未来,当真相公布后,星际文明的人类回望这一幕,定会庆幸……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零重力科幻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0gsf.com/a/17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