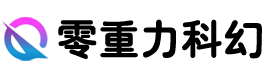电话铃像一只钻进耳朵里的铁皮甲虫,在死寂的小屋里没完没了地尖叫。我缩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那床薄得可怜的棉絮几乎裹不住骨头,每一次翻身都硌得生疼。四面墙皮剥落得厉害,昏黄的灯泡悬在头顶,光线浑浊,照着空荡荡的房间——一张床,一条被,一个油漆斑驳的床头柜,上面趴着那台同样掉漆的老古董电话机,是这屋里唯一能证明时间还在流动的东西。
又来了。推销保险?小额贷款?还是催缴那点可怜巴巴的、勉强够糊口的低保费?他们连我这种兜比脸干净的穷鬼也不放过,真是晦气到家了。我把脑袋往散发着霉味的枕头里埋得更深,用被子死死捂住耳朵。可那铃声顽固得像生了根,一遍,两遍,三遍……尖锐的声波钻过薄被,直刺脑仁。
“操!”我猛地掀开被子,赤脚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个箭步冲过去抓起那沉甸甸的黑色话筒,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你他妈有完没完?老子穷得叮当响,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再打来老子……”
“林先生?”一个异常平稳、毫无波澜的男声打断了我唾沫横飞的咆哮,像冰冷的金属滑过玻璃,“请您冷静。这里是‘创生纪元’生物科技集团总裁办公室。经确认,您与我们已故总裁林振寰先生存在法定继承关系。根据林总裁生前遗嘱,您将获得一笔总额为十亿元人民币的定向赠与。”
十亿?人民币?我像被一桶冰水从头浇到脚,火气瞬间冻结,只剩下骨头缝里透出的寒气,握着话筒的手不受控制地抖起来。电话那头还在说着什么“法律文件”、“身份验证”、“总部大厦”,声音遥远得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
“骗子!死骗子!”我对着话筒嘶吼,声音却干涩发颤,“创生纪元?老子听都没听过!十亿?你他妈怎么不说把月亮摘下来送我?” 我狠狠摔上话筒,那声巨响在空屋子里回荡,震得耳朵嗡嗡响。
可那串数字,“十亿”,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了脑子里。我喘着粗气,在狭小的房间里烦躁地转了两圈,目光最终钉死在墙角那台蒙着厚厚灰尘的老旧电脑上。那是我捡来的破烂,屏幕碎了一角,开机时风扇会发出拖拉机般的轰鸣。我扑过去,手指哆嗦着按下开机键。风扇果然开始嚎叫,屏幕艰难地亮起,闪烁了好几下才勉强稳定下来。
我在搜索框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近乎虔诚地敲下“创生纪元生物科技集团”。
回车。
屏幕瞬间被海量信息淹没。公司官网——设计得像未来城市的蓝图,流光溢彩。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基因疗法突破”、“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市值再创新高”……那些配图里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大厦,冰冷的金属质感,穿着白大褂或高级西装、表情疏离得像精密仪器的人……每一张图片,每一个标题,都像无形的巨锤,一下下夯在我脆弱的认知上。
十亿。那个冰冷的男声。这庞然巨物般的公司……是真的!
一股滚烫的、足以焚毁理智的狂喜猛地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十亿!低保!破床!以及那些狗眼看人低的白眼!全都滚他妈的蛋!这念头像岩浆喷涌,烧得我浑身颤抖,眼前阵阵发白。就在这狂喜的火焰几乎要吞噬一切时——
为什么是我?一个窝在发霉出租屋里的穷光蛋?那些自视甚高的领导者,那冰冷的大厦,以及电话里那毫无感情的男声......这泼天的富贵,为什么砸在我头上?
一丝冰冷的寒意,像毒蛇的信子,悄无声息地顺着脊椎爬了上来。
不!管他呢!那可是创生纪元!是真金白银的十亿!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跳了!岩浆霎时便以更猛烈的姿态吞没了那股寒冷的蛇,烧得渣都不剩!
甚至忘了穿鞋,我像一颗被点燃的炮弹,猛地轰开门,一头撞进外面浑浊的阳光里。
我像溺水者看到浮木,用尽全身力气扑向街边的出租车,一把拉开后车门就钻了进去,沉重的身体砸在冰凉的皮椅上。
“师傅!创生纪元总部!快!用最快的速度!”我几乎是在咆哮,心脏在肋骨后面疯狂擂鼓。
司机是个干瘦的中年人,从后视镜里瞥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惊愕和一丝鄙夷。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只穿了件洗得发白、领口松垮的破汗衫,赤着脚,头发乱得像鸡窝,浑身散发着廉价肥皂和隔夜汗馊的混合气味。
“下去!”司机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冷,“这车别人预定了!”
“我有急事!天大的急事!钱不是问题!我给你双倍!三倍!”我急红了眼,语无伦次。
“听不懂人话?下去!”司机提高了音量,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再不下我叫保安了!”
冰冷的现实兜头浇下。我像条被扔上岸的鱼,狼狈地被“请”出了那辆散发着皮革和空调冷气味道的出租车,赤脚踩在滚烫粗糙的柏油路上。那辆车绝尘而去,留下我一个人站在路边,像个可笑的傻子。阳光毒辣,晒得我裸露的皮肤发烫。我喘着粗气,望着远处城市中心那些在热浪中微微扭曲的、如同巨兽獠牙般的摩天大楼群,其中最高最冷冽的那一栋,就是目标——创生纪元大厦。
腿着去!十亿在招手,这点路算什么?我咬紧牙关,迈开腿,汇入街边汹涌的人潮。汗水立刻涌出来,顺着额角、脖子往下淌,在汗衫上洇开深色的痕迹。赤脚踩过滚烫的地砖、粗糙的水泥路、硌脚的小石子,每一步都钻心的疼。路人投来的目光像细密的针,带着好奇、嫌弃或漠然,刺在我身上。我死死盯着远处那栋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银光的大厦,仿佛它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支撑着我拖着越来越沉重的双腿向前挪动。
不知走了多久,腿脚麻木得像灌了铅。当我终于站在这座擎天巨柱般的建筑脚下时,巨大的阴影笼罩下来,几乎让我窒息。旋转玻璃门光滑如镜,映出我狼狈不堪的倒影: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赤着沾满黑灰的双脚,与这光洁如新、处处透着昂贵气息的环境格格不入。
我刚想往里冲,一个穿着笔挺深蓝色制服、身材高大壮硕的保安像一堵墙般无声地挡在了面前。他的眼神锐利如鹰,在我身上扫了一遍,眉头立刻拧成了疙瘩。
“站住。干什么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我找人!总裁办公室!他们打电话叫我来的!”我急切地辩解,声音因为疲惫和紧张而嘶哑。
“预约凭证?”保安伸出手,掌心向上,干净整洁。
预约?那电话里没说啊!“没有!但我真是林振寰的亲戚!他们叫我来的!十亿!遗产!”我语无伦次,试图从保安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找到一丝松动。
“没有预约,不能进入。请离开。”保安的语气毫无波澜,像在陈述一条物理定律。他微微侧身,一只手看似随意地搭在腰间的警棍上,姿态充满了无声的警告。
完了。十亿就在眼前这栋楼里,我却连门都进不去。巨大的失望和屈辱感攫住了我,像冰冷的潮水漫过头顶。我像被钉在原地,赤脚踩在冰冷光洁的大理石上,寒气直往上冒。就在这时,身后旋转门的光滑玻璃上映出另一个身影。
一个年轻女人快步从电梯厅方向走来。她穿着剪裁完美的米白色西装套裙,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利落的“哒哒”声,像精准的秒针。她妆容精致,一丝不苟,神情是那种久居高位者特有的、近乎冷漠的平静。她径直走到我和保安之间,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没有惊讶,也没有鄙夷,只有纯粹的审视,像是在确认一件物品的编号。
“林先生?”她的声音如同她的外表,清晰、平稳,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起伏。
我像抓住救命稻草,拼命点头,喉咙干得发不出声。
“跟我来。”她简洁地吐出三个字,转身便走,甚至没有再看那保安一眼。保安立刻恭敬地退开一步,垂下目光。我赶紧跟上,赤脚踩在冰凉如镜的地面上,留下一个个污浊的脚印,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这地方的某种神圣秩序。
电梯无声而迅捷地上升,失重感让我胃里一阵翻腾。电梯门打开的瞬间,巨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一整层楼,空旷得令人心慌。巨大的落地窗环绕四周,将整座钢铁森林般的城市踩在脚下,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进来,照亮了纤尘不染的空气。整个空间里,只有一张长得不可思议的黑色会议桌,像一条沉默的河流,横亘在光洁的地板中央。桌子的另一端,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穿着深色的、一看就价值不菲的西装,神情肃穆,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像三台精密的扫描仪。
西装女人示意我在靠近我这端的唯一一张椅子上坐下。椅子宽大、冰冷、坚硬。我小心翼翼地坐下,感觉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对面中间那个头发花白、面容严肃的男人没有起身,也没有寒暄。他拿起手边一个薄薄的牛皮纸文件袋,手腕轻轻一抖,那袋子便沿着光滑如镜的桌面滑了过来。袋子滑行的时间长得令人尴尬,清晰地丈量着这张桌子的长度,也丈量着我和他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巨大的鸿沟。
“林先生,”花白头发的男人开口,声音低沉而公式化,“这是林振寰总裁生前委托我们执行的遗产赠与协议,以及一份必要的医疗免责声明。请仔细阅读,然后在最后一页签名处签字。签完字,资金会在您完成指定医疗程序后即刻转入您名下的专属账户。”
我的手指因为紧张而冰凉僵硬,几乎不听使唤。我笨拙地解开文件袋的线扣,抽出里面雪白挺括的纸张。密密麻麻的文字像一群群蠕动的黑色蚂蚁,看得我头晕眼花。什么“法律关系”、“权利义务”、“不可抗力”、“风险告知”……这些字眼对我来说如同天书。我烦躁地、几乎是粗暴地翻动着纸张,纸张发出哗啦啦的脆响,在这过分安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
我的目光瞬间被钉死在那个数字上。
人民币:1,000,000,000元(壹拾亿元整)
后面跟着一个需要签名的空白横线。
十亿!真的是十亿!后面那些蚂蚁般的“免责条款”、“可能风险”、“实验性质”的小字,瞬间变得模糊不清,失去了所有意义。我的呼吸骤然停止,血液轰的一声冲上头顶,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狂热而虚幻的红光。
笔!我需要笔!我慌乱地在桌面上摸索,像个渴极了的旅人寻找水源。西装女人无声地递过来一支沉甸甸的银色金属笔。我一把抓过,冰凉的触感让我哆嗦了一下。我甚至没有再看那冗长的文件一眼,所有的注意力都凝聚在那条横线上,凝聚在那串足以改变我卑微如尘一生的天文数字上。我用尽全身力气,在那条线上歪歪扭扭、颤抖着写下了我的名字——林小树。字迹丑陋,像几条被踩死的蚯蚓。
笔尖离开纸张的瞬间,一种巨大的、近乎虚脱的狂喜攫住了我。成了!十亿是我的了!
“很好。”花白头发男人微微颔首,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波动,“协议生效。接下来,请林先生配合我们前往集团旗下的‘纪元生命’医院,完成指定的医疗程序。这是赠与生效的必要前置条件。”他朝西装女人示意了一下。
西装女人立刻走到我身边:“林先生,请跟我来。”
我晕乎乎地站起来,脚步发飘,像个梦游的人,跟着那清脆的高跟鞋声,离开了这片冰冷奢华、如同神祇殿堂般的空间。十亿的光环笼罩着我,让我感觉不到脚下的冰凉,也感觉不到身后那几道审视的、意义不明的目光。
“纪元生命”医院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更像一座未来主义的堡垒。纯白色的走廊一尘不染,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和某种冰冷金属混合的气味。没有嘈杂的人声,只有偶尔响起的、节奏单调的电子提示音。我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泛着冷光的金属手术台和几台造型怪异、闪烁着幽蓝指示灯的机器。几个穿着浅蓝色无菌服、只露出眼睛的人围了上来,动作麻利而沉默。他们让我换上同样冰冷的病号服,躺上那张坚硬如铁的台子。
“局部麻醉,配合微创神经介入,全程无痛感,请放松。”一个毫无情绪起伏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像是机器的合成音。
冰冷的消毒棉球擦过后颈和头皮,带来一阵激灵。接着,一种微凉的液体被注入。很快,从脖子往上,一种奇异的麻木感像潮水般蔓延开来。头被固定在特殊的支架上,无法动弹。视野被一个弧形的、布满细小孔洞的金属罩子遮挡了大半。我能清晰地听到耳边响起细微的机械运转声,“嗡——滋滋——”像某种精密的昆虫在低鸣。轻微的震动从头皮传来,接着是极其细微的、几乎感觉不到的穿刺感,仿佛有极细的冰针探入。没有痛,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被异物侵入的异样感,以及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我睁大眼睛,视野里只有金属罩子冰冷的反光和上方刺眼无影灯模糊的光晕。
意识在冰冷的机械嗡鸣和消毒水的气味中,慢慢沉入一片混沌的、不安的黑暗。
……
意识像是从深海里艰难地浮上来。眼皮沉重得像压着石头。我费力地睁开眼。
头顶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景象——斑驳发黄的天花板,角落里挂着蛛网,那盏昏黄的老灯泡静静地悬着。身下是那张硬邦邦、硌得骨头疼的木板床。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混合着霉味和灰尘的气息。
梦?
一个荒谬绝伦、光怪陆离的梦?十亿?创生纪元?手术?我猛地坐起身,心脏狂跳,下意识地抬手摸向后脑勺。
指尖触到的不是柔软的头发和头皮,而是一小片微微凸起的、带着粗糙颗粒感的疤痕。疤痕不长,约莫两寸,横在后脑偏下的位置。触感冰凉、坚硬,与周围温热的皮肤截然不同。指尖划过那疤痕边缘时,一种细微的、仿佛电流窜过的酥麻感直刺大脑深处。
不是梦!
一股混杂着狂喜、荒诞和一丝莫名恐慌的激流瞬间席卷全身。十亿!我的十亿呢?我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空荡荡、家徒四壁的房间里疯狂扫视。钱呢?支票?银行卡?什么都没有!巨大的失落感刚涌上来,视野的右下角,极其边缘的位置,极其微弱地,毫无征兆地闪烁了一下。
我下意识地、近乎本能地将全部注意力凝聚到那个视野的角落。
仿佛按下了某个无形的开关,一行清晰无比的、散发着幽蓝色微光的数字,静静地悬浮在了那个角落:
1,000,000,000.00
十亿!它就在那里!像一个嵌入我视觉神经的幽灵,一个只属于我的、冰冷的奇迹!
我张大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撞碎肋骨。我伸出手,颤抖着在眼前挥舞,那串数字纹丝不动,稳定得如同宇宙常数。我闭上左眼,它还在。闭上右眼,它还在。它不属于物理世界的光影,它就烙印在我的感知里!
巨大的、不真实的狂喜再次淹没了我。我像个疯子一样从床上跳下来,赤脚在原地转了几个圈,然后猛地拉开那扇破木门,冲了出去。我需要空气,需要人群,需要立刻、马上、去感受这十亿带来的翻天覆地!
午后的街道嘈杂而闷热。阳光刺眼。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脚步虚浮,像踩在棉花上。目光贪婪地扫过街边的一切,仿佛第一次真正看见这个世界。卖水果的小贩、疾驰而过的电动车、牵着孩子的妇人、玻璃橱窗里诱人的商品……我的目光掠过街角那家小小的便利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零食包装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走了进去。冰凉的空调风夹杂着关东煮和烤肠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货架上,一包印着卡通图案的薯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就在我的目光聚焦在那包薯片的瞬间,一行细小的、同样散发着幽蓝微光的数字,毫无阻碍地叠加在了薯片包装袋上:
¥7.50
就像那十亿的数字一样清晰、直接。
一个念头,纯粹出于好奇和一种刚刚获得“超能力”的兴奋,在我脑中闪过:买它!
念头刚起,视野右下角那庞大的十亿数字,最末端的“.00”轻轻一跳,变成了“.50”。小数点前则变成了一个“3”前一串的“9”。
几乎同时,便利店收银台方向传来一声清脆的、带着欢快旋律的电子女声:“支付宝到账——七点五元!”
收银员疑惑地抬起头,左右看了看,没发现拿着手机支付的顾客,脸上露出一点茫然。
我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随即又沸腾起来!它……它能用!真的能用!只要我想!这念头本身就是支付!巨大的兴奋让我几乎要叫出声。我猛地转头看向店里的其他东西,目光所及之处,幽蓝色的数字标签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浮现:
冰柜里的罐装可乐:¥3.00
收银台边的热狗:¥6.00
货架上的进口巧克力:¥45.80
店员身上那件印着便利店LOGO的蓝色T恤:¥29.90 (这个标签让我愣了一下)
甚至,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我看到外面驶过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视野自动聚焦拉近,一行清晰的蓝色标签打在它光亮的车身上:¥850,000.00
街对面那栋几十层高的写字楼,一个巨大的蓝色数字悬浮在楼顶:¥285,000,000.00
一个穿着光鲜、拎着名牌包的女人匆匆走过,标签闪现:¥1,235,600.00 (包含了包、衣服、首饰?)
另一个穿着工装、扛着工具的民工大叔走过,标签则短得多:¥3,500.00 (是他身上的工具价值?还是……某种估算?)
万物皆标价!整个世界在我眼中,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明码标价的超级市场!而这十亿,就是一张几乎无限额度的、意念驱动的超级信用卡!
狂喜如同海啸,彻底吞没了我。我像个闯入糖果店的孩子,猛地扑向货架,手臂疯狂地扫荡:薯片、虾条、巧克力、牛肉干、进口果汁、雪糕杀手……购物篮瞬间被塞得满满当当,甚至溢了出来。每塞入一件,视野右下角的数字便轻快地跳动一下,那小数点后的变动在庞大的基数前,渺小得如同尘埃。收银员看着我堆成小山的零食和一身破旧的打扮,眼神复杂,充满了难以置信。我毫不在意,抱着巨大的、沉甸甸的塑料袋冲出便利店,迫不及待地撕开一包薯片,咔嚓咔嚓地大嚼起来,咸香酥脆的味道混合着挥金如土的快感,简直妙不可言!
就在这时,我的脚步顿住了。
在便利店旁边一条堆满杂物、散发着淡淡馊臭味的狭窄小巷口,一个小小的身影蜷缩在那里。
那是一个小女孩。大概八九岁的样子,瘦弱得像一根在风中瑟瑟发抖的芦苇。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明显不合身的旧T恤,下摆几乎垂到膝盖,宽大的领口露出嶙峋的锁骨。裤子也又旧又短,膝盖处磨破了两个洞。赤着脚,脚上沾满了黑灰。她低着头,枯黄打结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掉了漆的破旧铁皮罐子,里面零星躺着几枚硬币。
我的目光落在她身上。视野里,一个数字安静地浮现出来:
¥0.00
零?一个活生生的人,价值是零?
这个数字像一根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刺穿了我刚刚被十亿填满的狂喜泡沫。一个模糊的、几乎被遗忘的影像瞬间闪过脑海
[我知道我们家有钱][但有钱的是我们家,不是我][我对我父母,了解的不多]很多年前,似乎也有这样一个蜷缩在角落、无人问津的瘦小身影,只是那张脸早已模糊不清。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感,混合着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刺痛,猛地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犹豫了一下,鬼使神差地抱着那袋沉甸甸的零食,慢慢走了过去。脚步在女孩面前停下,阴影笼罩了她。
她受惊般猛地抬起头,露出一张脏兮兮的小脸。算不上漂亮,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她的脸颊有些凹陷,皮肤也透着不健康的黄气。但那双眼睛,在瘦小的脸上显得格外大,黑白分明,清澈得像山涧里的泉水,此刻却盛满了惊慌和恐惧,像只被逼到墙角的小兽。她下意识地把那个破铁罐子抱得更紧,身体往后缩了缩,似乎想把自己嵌进身后的墙壁里。
那双清澈而惊恐的眼睛,像一面镜子,瞬间映照出我曾经的卑微和不堪。喉咙有些发紧。我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动作不那么突兀。我拉开鼓囊囊的塑料袋,里面五颜六色的包装袋散发出诱人的食物香气。我拿出好几包薯片、几袋独立包装的蛋糕、几瓶果汁,一股脑地塞到她怀里。
“拿着,”我的声音有点干涩,“给你的。”
女孩完全愣住了,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茫然。她看看怀里突然多出来的、散发着香气的食物,又看看我,小嘴微张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吃吧。”我笨拙地补充了一句,站起身。没有再停留,抱着剩下的零食,转身快步离开了那条阴暗的小巷。身后,似乎传来一声极其细微的、带着哽咽的吸气声。我没有回头。
这点微不足道的给予,很快被淹没在十亿喷涌的神力中。
我像蜕壳的昆虫,一头扎进顶级商场。当导购们鄙夷的目光在我随手买下五位数的衬衫(¥18,800.00)后瞬间化为谄媚时,一种扭曲的快感窜遍全身。昂贵的西装、锃亮的皮鞋、一丝不苟的发型——全程看着镜中的油腻邋遢变成那个焕然一新的“精英”时,一种混合着虚荣和征服感的巨大满足感窜遍全身。
发霉的小屋成了历史。我住进云端般的顶层复式,窗外是璀璨的钻石星河;顶级豪车成了玩具,引擎的咆哮是新的乐章;米其林三星成了食堂,金钱的味道在味蕾上醇厚绽放。聚会、游艇、私人飞机……纸醉金迷的漩涡将我牢牢吸住。
起初,我还看着视野右下角那庞大的数字(1,000,000,000.00)随着每一次挥霍轻微跳动,像个拥有无限弹药的玩家。但十亿太庞大了!庞大到小数点前的位数似乎永不减少。很快,那串数字便从意识焦点中淡出,沉没在视野边缘,被眼前不断变幻的、令人迷醉的感官洪流彻底淹没。它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背景板,一块证明我拥有无穷力量的冰冷符号。
我彻底沉沦在这唾手可得的幻梦里,追逐着更高、更快、更刺激的消费巅峰,不再关心数字本身。每一次无声的跳动,都只是十亿长城上被悄然搬走的一块砖石。
时间在挥霍中失去了刻度。直到某一天,在某个顶级俱乐部彻夜狂欢后的清晨,我在市中心顶层公寓那张能容纳五六个人的、铺着埃及棉床品的大床上醒来。
宿醉带来的头痛像有凿子在脑子里敲打。我习惯性地睁开眼,想看看窗外刺眼的阳光。
黑暗。
绝对的、令人窒息的黑暗。
不是房间没开灯的那种昏暗,而是仿佛置身于宇宙最深邃的虚无,没有任何一丝光线的存在。我猛地坐起身,心脏骤然缩紧,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
怎么回事?瞎了?
恐慌如同冰冷的毒蛇,瞬间缠绕住我的咽喉。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在眼前疯狂挥舞。没有视觉!什么也看不见!我的手呢?我的手在哪里?为什么感觉不到?!我试图去摸自己的脸,胡乱摸了一气——没有触觉!皮肤的感觉消失了!能够感受到的只有一片虚无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空洞!
啊——!我让自己大吼一声,但我听不到!耳朵里只有一片死寂,绝对的、真空般的寂静!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喉咙的震动!我猛地吸气——没有味道!鼻子像被彻底堵死,任何气味都消失了!消毒水?香水?宿醉的酒气?什么都没有!仿佛整个世界的感官信号被瞬间切断!
不,应该说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喉咙,我的鼻子——我感受不到它们在哪里!我的身体,我感受不到它在哪里!
绝对的黑暗!绝对的死寂!绝对的虚无!
我在哪里?我动了吗?我还在床上吗?巨大的、足以吞噬灵魂的恐惧将我彻底淹没。我像一个被抽掉所有感官的幽灵,被遗弃在混沌的虚无之中。我凭着记忆和本能,试图翻身下床,但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感觉不到身体的平衡!我不知道自己是在站着还是坐着,亦或是趴着,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唯一能知道的,是我在让自己动!
“系统提示:您的账户已被冻结。”
一行冰冷、僵硬、散发着微弱红光的文字,突兀地、霸道地撕裂了这片吞噬一切的黑暗,直接烙印在我的“视野”中央。像判决,像讣告。
账户冻结?冻结?!那十亿?!是它!是那个该死的脑机!
巨大的恐慌和一种被愚弄的滔天愤怒瞬间炸开!骗子!全是骗子!什么狗屁亲戚!什么十亿馈赠!都是骗局!他们偷走了我的感官!把我变成了一个活着的幽灵!
我不能待在这里!我要出去!我要找人!我要……我要……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恐惧。我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这一刻竟又有了些许微弱的感觉。凭着记忆中对房间布局的模糊印象,用尽全身的力气,手脚并用地在冰冷的地板上(感觉不到冰冷)向前爬行(感觉不到移动的摩擦)。撞到障碍物,就摸索着绕开(感觉不到障碍物的形状)。不知道爬了多久,或许只有十几秒,或许像一个世纪。终于,指尖触碰到了一面光滑、冰冷的平面——门?墙?我疯狂地拍打着,摸索着,寻找着门把手的位置(感觉不到金属的冰凉和形状)。终于,一个凸起!我猛地按下、拉开!
一股微弱的气流拂过身体(感觉不到温度)。外面!是外面!
我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脚下似乎踩到了坚硬的地面,但我感觉不到。我不知道自己身在几楼,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周围有没有人。只有那行刺眼的红色冻结提示,像一盏血红的灯笼,高悬在黑暗的虚空之中,是这绝对虚无世界里唯一的存在。
我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开这栋该死的楼!
我凭着本能,朝着记忆中电梯间或者楼梯间的方向,跌跌撞撞地狂奔(感觉不到脚步的落下)。身体在黑暗中踉跄、碰撞(感觉不到疼痛),像个失控的提线木偶。冲过一个转角,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光滑的斜坡(台阶?),身体猛地向前扑倒,翻滚下去(感觉不到撞击和翻滚)。不知滚了多少级,最后重重地砸在坚硬的地面上(依旧无感)。我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向前冲撞。
前方似乎有更强烈的气流和更嘈杂的……某种震动?虽然听不到,但身体似乎能感受到空气的震荡。
是出口!一定是出口!马路!
希望像微弱的火星闪过。我朝着那个方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像一颗被绝望射出的炮弹,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就在我的身体(感觉不到肢体)冲出某个界限的瞬间——
“砰!!!”
一声沉闷得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巨响,并非通过耳朵,而是直接、狂暴地轰击在我的意识核心!
剧痛!
无与伦比的、撕裂一切的剧痛!
像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又像被高速行驶的列车拦腰撞碎!骨骼碎裂、内脏挤压、肌肉撕裂……所有被屏蔽的痛觉神经,在这一刻被强行接通,放大到极限!恐怖的痛楚洪流瞬间冲垮了意识的堤坝!
啊——!!!
在意识被这灭顶的剧痛彻底撕碎、陷入永恒的黑暗之前,最后一丝模糊的“感知”碎片般掠过:
视野里那片血红刺目的冻结提示,像接触不良的屏幕,剧烈地闪烁、扭曲了一下。
黑暗的边缘似乎被撕开一道缝隙,有刺目的白光涌入。
白光中,几个模糊的、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影,正快速地向自己倒下的位置靠近。
车门打开的声音?脚步声?……所有的声音和画面都如同隔着一层厚厚的、沾满血污的毛玻璃。
一个冰冷的、毫无情绪的男声,仿佛直接植入脑海的电子音,断断续续,成为意识沉入虚无前捕捉到的最后信息:
“…实验体…编号21…感官剥夺…躯体正常......”
“回收…完成…”
(未完待续)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零重力科幻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0gsf.com/a/17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