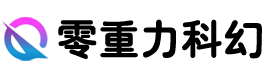终结不是终结
核战176年后,地球被永恒灰雪覆盖。
我是携带人类最后胚胎的守护者,踏过千里死寂去往传说中最后的图书馆。
冰层下的老学者却告诉我:“文明的火种是个残酷谎言。”
当胚胎长出鳃鳞倒刺,我才惊觉人类基因早已被缓慢辐射扭曲。
我跪在冰面上焚烧全部资料时,变异鱼群却在冰下汇成新星座。
“埋葬他们,”老学者声音穿冰而来,“让新世界真正诞生。”
我最后看了看胚胎舱里跳动的小手,打开闸门。
风雪永无休止。它们从天顶的混沌中倾泻而下,不是记忆中脆弱的六角冰晶,而是沉甸甸、黏腻的灰色粉末,带着辐射测量仪都难以完全捕捉的深层衰变气息。176年,足以让这灰烬之雪成为大地的第二层皮肤,埋葬山脉,覆盖海洋,抹平城市,把世界简化为一片起伏不定、吞噬一切的坟茔。寒冷像一种有知觉的生物,顺着装备每一个细小的缝隙爬进来,啃噬着骨髓。我拉紧了冻得像铁皮一样僵硬的皮毛兜帽,唯一的声音是雪橇滑板碾过压实雪面发出的单调嘶鸣,还有我自己沉重缓慢、带着冰渣的呼吸。
我叫苍衣。名字是一个在冰层深处长眠的女人给的,她说那是“灰雪”的意思,像这永世的裹尸布。而现在,这裹尸布下,紧贴着我因寒冷和辐射而布满紫红色斑块的胸口,藏着这个时代的唯一禁忌与希望——一颗巴掌大的低温胚胎储存舱。它像一个悖论般存在着,金属外壳冷得能粘掉皮,内部却恒久地跳动着微弱的红光,代表那三个生命体原始心脏的搏动。旧时代的胚胎,人类,最后的……希望?或者说,仅剩的最后一点念想。
使命压在肩上,比覆盖世界的永冻层更沉重。横穿“灰烬平原”,目标是传说飘渺的“磐石要塞”,一座在浩劫前建造的巨大知识圣殿,深埋于古老冰川之下。传说中,那里收容着最后的知识,庇护着最后的学者,是文明仅存的火种之地。这是我母亲,还有我母亲的母亲,代代用生命守护的秘密和交付的使命。我们称之为“火种计划”——藏匿、传递、蛰伏,等待辐射减弱、地表回暖、冰雪消融的那一天。那时,胚胎需要知识,知识需要生命,生命将重新点燃火焰。
一千多个被死寂统治的昼夜后,风雪骤然减弱。前方,不再是令人绝望的平缓雪原。一座巨大得撕裂视野的纯黑壁垒骤然升起,如同沉睡在冻土中的古老神灵裸露的脊梁。冰冷的山岩上覆盖着厚度超过百米的万古冰川,冰川的蓝色深处,却凝固着无数扭曲的钢铁巨构,那是旧时代城市被寒冰吞噬、挤压变形后的残骸。它安静得令人窒息,带着一种冻结时间的威严。冰川底部,一道不起眼的缝隙——一个被永恒冰层切割出来的幽暗入口。磐石要塞就在这巨冰之下。
入口比想象中艰难。厚重的隔热装甲门,如同旧时代的叹息般开启缓慢,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挤压声。更厚的冰雪被凿穿,才露出一小段通往幽深冰下的竖井。刺骨的、混着金属腐蚀和某种冰冷霉味的空气涌出。一条几乎垂直的梯子向下延伸,深不见底。我徒手爬下,每一次手指触碰冰冷的金属梯级,麻木都加重一分。唯一的光源是我头盔上摇晃的光柱,扫过厚实的冰壁,偶尔映出冰封在里面的模糊黑影——像是被冻结在惊恐中的某个前代人类。
仿佛穿透了地球的表层,终于落在一条人工开凿的甬道底部。空气冰冷依旧,却奇异地比地表稍“暖”一些。死寂更深,像沉入了水银的海洋。甬道尽头,一片幽蓝的微光渗透出来,带着非自然的质感,那是冻僵了的荧光。光源来自一个宽阔无比的洞穴——一座被深埋冰川覆盖包裹的巨大地下空间。幽蓝的光来自覆盖洞壁、穹顶乃至巨大石柱的奇异厚重苔藓和珊瑚状结晶。它们的冷光勾勒出一座座书山的轮廓,一直延伸到高处黑暗的阴影之中。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冰冷气息——旧纸张的霉味,尘埃,还有一种……近乎悲伤的味道?不,不是悲伤,是某种更深邃更平静的空寂。这是图书馆,但更像陵寝。一座埋葬人类知识的巨大冰冢。
光影在庞大的书架群间流动,冰冷的蓝色光晕勾勒出一个瘦小佝偻的身影。他就站在一片书籍的废墟之上,身旁堆叠着打开的、被随意翻检过的书籍。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极其缓慢地转过了身。岁月如同冰雕一样刻在他的脸上,皮肤苍白到近乎透明,布满蛛网般的深色血管和老人斑,像一张古老羊皮纸。厚厚的毛皮大衣在他身上显得过于巨大,而他的眼睛……那双眼睛的瞳孔似乎因为常年适应地下环境而异常扩大,但瞳孔的边缘却是浑浊的灰蓝色,像是蒙了一层冰川的污迹。
“守护者?”声音穿破死寂,嘶哑如砂纸摩擦枯骨,带着极其微弱、怪异的气流共鸣,像声音同时在冰层中回荡,“真是……”他顿了一下,那只覆盖着斑点和皱纹的手抬起,极其缓慢地挥动了一下,“一个……不祥的征兆。‘火种’送来了。”他眼中没有丝毫喜悦的光芒,只有洞察一切的深邃的沉静。
我叫苍衣。那冰冷沉重的胚胎舱在我怀中,似乎能感受到此地非同一般的死寂。我向他展示了舱体上那微弱的红灯:“需要知识……激活系统……设定苏醒环境……培养方案……”每一个字吐出,都带着白雾。资料在我贴身携带的密封包里,硬得像一块寒冰。
奥列格(这是他给我的名字,如同在咀嚼一块坚冰)浑浊的灰蓝色眼珠盯了我很久很久,目光似乎穿透了我厚重的防护和冻伤的皮肤,直抵骨髓深处某个我自己都未觉察的角落。他的喉咙里滚动着干涩的咕哝声。
“跟我来。”
他像冰层中缓慢漂流的幽灵,穿过庞大书架的阵列,走向这个洞穴更深处某个灯光未能覆盖的角落。那扇暗门隐藏在一面堆满厚重地质图册的书墙后,开启时几乎听不见任何声响。里面的空间逼仄、寒冷,充满刺鼻的化学消毒剂气息和电子设备老旧运行发出的嗡鸣。一排排布满灰尘的机器发出微弱的呼吸般的蓝光。
“放下‘火种’,”奥列格指示角落一个被清理出来的金属台面,上面布满了凌乱纠缠的线缆接头,“链接监测系统。”
胚胎舱被小心地置入一个特殊接口。舱体红灯闪烁几下,连接成功。一阵微光闪过旁边的老式光幕。三维胚胎图像瞬间在光幕上展开。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图像在旋转、放大,清晰无比。一颗小小的、仍在微弱搏动的胚胎心脏旁,本该是光滑皮肤覆盖的地方,生长着一层细密、半透明、仿佛鱼类的鳞片。胚胎尾端尚未成形的小小肢体根部,有锐利的角质凸起如倒刺般刺出。头部覆盖着稀疏的毛发,但耳廓的位置,却是两个薄得几乎透明的、有着复杂褶皱的……鳃裂。微弱的心跳在冰冷的实验室里敲击着我的耳膜,砰……砰……
“辐射,”奥列格嘶哑的声音紧贴着我的神经响起,每一个字都像冰块砸落,“从未‘减弱’,守护者。它只是……学会了潜伏,学会了雕刻。176年,足够它一点点、一代代重写你们守护者的密码,直到孕育全新的……蓝图。”
冰冷实验室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胶体,每一次试图呼吸都像在撕扯胸腔里冻结的血肉。眼前光幕上那个扭曲的胚胎还在无意识地搏动,微弱,却无比顽强。细密的鳞片纹理在幽蓝冷光下闪烁着非人的光泽,那根根微小却锐利的骨刺,那清晰的鳃裂褶皱……像无数根烧红的针,刺穿了我意识里最根本的依托——母亲传下的使命,祖辈燃烧生命传递的那个“火种计划”。整个世界的重量轰然崩塌,直接压在我的脊梁上。我双腿一软,重重地跪倒在地,膝盖撞击冰冷金属甲板的声音在死寂的实验室里回荡了一下,随即被无边的冰冷吞没。头盔面罩上糊着一层自己呼出的、瞬间凝结的白霜,我死死盯着那具承载了所有希望,也刻满了所有背叛的胚胎。
“他们……都在被……改造成这样?”喉咙仿佛被冰碴塞住了,嘶哑得连自己都认不出。声音在面罩里回荡。
奥列格没有立刻回答。他像一尊冰川裂隙里的石像,浑浊的蓝灰色瞳孔倒映着光幕上那怪异的影像。然后,他极其缓慢地点了一下头,干枯、花白的头发几乎纹丝不动。“你们……所有的守护者。一代,又一代。‘火种’计划最核心的保密机制,正是它最大的毒药。你们世代隔离,近亲耦合,辐射的刀锋,就在你们遗传的血脉里一代代加深刻痕。你们在永冻的地穴深处保存胚胎,隔绝地表,却也错失了一线……适应的可能。”他那只布满黑褐色斑点、指关节扭曲变形的手,极其迟缓地抬起,指向我沉重的防护服,接着指向胚胎光幕下闪烁着的代表我们这一支守护者族系根源的数据流。那冰冷的数据洪流正在眼前无声滚动,像一场末日的雪崩。“数据……不会说谎。你们的族群基因……早已崩溃。从第109年开始,连续五代出生个体的突变积累分析……还有地表深层冻土采样显示的辐射沉降粒子半衰期……”他浑浊的眼睛最终落回到我身上,目光穿透厚实的面罩,带着一种近乎冰冷的悲悯,“它只是……在等待时机。在等着你们,将它的‘杰作’……重新带回这个世界。”
那悲悯如同一把烧红的铁钎,直接捅穿了最后一丝侥幸。我猛地抬手,撕裂贴身密封包冰冷搭扣的动作近乎疯狂。那些纸质资料——泛黄卷边、字迹模糊、浸染着几代守护者体温和偶尔冻伤渗出的暗红——带着冰碴,滑落在脚边冰冷的地板上。承载着火种希望的文字和图纸,此刻像是一堆被遗弃的裹尸布。
“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每一个字都像肺里挤出来的冰渣,沉重得要把我压垮。是疑问,更是绝望的最后确认。
奥列格浑浊的目光掠过我脚下散乱的资料,再次缓缓转向那悬浮在空中的、正投射着胚胎畸变影像的光幕,接着,目光似乎穿透了头顶厚厚的冰岩层,投向了实验室之外更广袤而冰冷的世界。那浑浊的瞳孔深处,仿佛倒映着洞穴穹顶那片散发着幽蓝寒光的奇异苔藓和结晶。他喉咙里发出一阵意义不明的、仿佛冰川摩擦的低沉轰鸣,过了一会儿,嘶哑的声音才重新组织成形,穿破我意识的混沌:
“生命……自有其道。只是……我们的眼睛太久地,只望向过去燃烧的灰烬……而拒绝看清冰雪之下,已亮起的星芒。你们带不来暖春,守护者。你们所能带来的……只是更深的寒冬,和一个注定扭曲的新生。”他停顿了很久,像是积聚最后的力量,然后那冰冷的声音带着某种洞彻一切却又无比沉寂的穿透力,缓缓流入我已被碾碎的意志,“埋葬他们吧。让……真正的……诞生。”
我踉跄着站起,用尽全身力气扛起那个沉重、冰冷的胚胎储存舱,每一步都踏在祖先遗骸幻化的尘埃之上。幽蓝色的书籍废墟在身边延绵,如同一座巨大的冰墓。奥列格像一块沉默的冰岩,凝固在光幕前,没有回头。冰冷的气息浸透防护服,死死缠绕。
厚重的闸门缓缓滑开,外面是磐石要塞中唯一能见到真实“天空”的地方——一片被冰川拱卫、顶部开有巨大垂直冰隙的深潭边缘。潭水漆黑如墨,深不见底,水面绝对地静止,光滑得像一块凝固的玄冰。我走到悬在水潭边缘的狭窄金属平台上。防护服关节在刺骨的寒气里吱呀作响,每一次细微的声音都被这片死寂放大。
头顶数百米处,冰隙开口狭窄,只能看到一线永不停息的灰雪飘落,纷纷扬扬,落入下方深沉的黑暗。潭水漆黑,像吸收了世间所有的光。时间也仿佛冻住了。我慢慢弯腰,将沉重的胚胎储存舱放在冰冷的金属台上,双手覆盖在冰冷的舱盖上。那点微弱的心跳隔着厚厚的复合材料和防护手套传递上来,细微但顽强。我掀开舱盖,低头看去。
微弱的红灯映照下,其中一个胚胎动了。尚未成形的肢体无意识地弹动了一下,小小的、覆盖着细密半透明鳞片的手掌向上伸展了一下,五个蜷缩的小小指头微微张开,指尖的角质小刺在红光下闪动着致命的微芒,像某种来自深渊的邀请。冰冷的水汽渗入脖颈,冻得我狠狠一个激灵。
“真正的……诞生……”
奥列格的话语在我脑中再次冰冷地滑过。就在这一刻,平静如镜面的漆黑深潭深处,毫无征兆地亮起了一点微光!幽绿色的,极其微弱。紧接着,是第二点、第三点……无数幽绿色、莹蓝色、甚至淡紫色的微光,如同被无形的丝线串联,缓缓上升!
光点迅速接近水面。变异的鱼群!它们没有眼睛,或是顶着一团发光的感光组织,头部生长着长长的发光触须。暗色的鳞片上覆盖着类似外骨骼的坚硬甲壳。更诡异的是,它们彼此吸引,竟在水中无声地汇聚、排列!不是混沌一团,而是逐渐聚拢成一个无比精确、复杂、带有几何美感的、不断缓缓旋转的螺旋状图案!幽绿、深蓝、淡紫的冷光在绝对黑暗的深渊里,组合成了一个缓慢自旋的、流动的巨大几何星座!光芒透过上方冰隙落下的一线微光,交织在一起。一种无声的、冰冷而浩瀚的生命韵律,在黑暗中搏动、弥漫开来,仿佛在无声地宣告着这片死寂世界的新主宰。
这螺旋的光芒映入我覆满冰晶的头盔面罩。我最后的视线凝固在胚胎舱里,那个畸形、覆盖鳞片的小手上,带着令人心碎的毁灭意愿——那里已孕育着旧时代的废墟。然后,手指移动,在控制面板上几个早已设定好的冰冷按钮滑过。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感觉了。只剩下一种被深寒潭水浸透的寂静——那是比核冬天的灰雪更古老的寂静。
“咔哒……”
储藏舱内部的某个结构应声释放。舱体下方的金属豁口无声滑开。那颗跳动着的、在微光下闪烁着诡异鳞片和小刺的胚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温柔却又无比决绝地推出,脱离金属壳,脱离束缚。
它向下坠去。像一粒过于沉重的灰烬,无声无息地沉入脚下那片绝对漆黑、闪烁着冰冷几何星光的深潭。漆黑的潭水瞬间吞没了它,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仿佛从未有任何存在落下过。
只有那些缓慢旋转的巨大几何星座在幽深的水中永恒而冰冷的变换形态,那流动的光芒穿透数十米厚的冰层。灰雪,如天谴的尘埃,穿过高高的冰隙,永不停歇地落向深渊。我站在原地,成为冻结在平台边缘的一具标本。头顶是灰烬,脚下是星空。世界的指针,在这一刻,无可逆转地跳向下一个刻度。冰层之下,一个新的生命螺旋,正缓缓转动。
奥列格站在厚重的观察窗前,苍白枯槁的脸紧贴在冰冷到几乎冻结的厚玻璃上。浑浊的灰蓝色瞳孔,在下方深潭中那片无声流动的冰冷几何星座幽光映照下,反射出异常的光芒。那光芒不含人性悲悯,也不含造物主的审视,更接近一种冰层深处观察微生物聚散的……纯粹静观。
远处,隔着巨穴层层叠叠的书架废墟,一声低哑到几乎被死寂吞噬的闸门关闭声隐隐传来。随后,只有永冻冰层自身的低频率嗡鸣,以及那无处不在、冰冷幽蓝的苔藓微光,才是磐石要塞恒久的背景。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零重力科幻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0gsf.com/a/17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