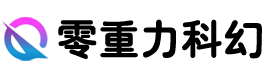趁着退潮时沙岸裸露,我凭舟登上岸。毕竟是农历的十四日,退潮的幅度相当大:以前未经踏足的地方全都显现出来,一些拐弯的地方堆积了一些黑泥,在那里耕作一定很合适。喔,好久没坚坚实实地踩在土地上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摇摇头,记不清。
沙岸很大,近处是沙,远处是泥。泥中插着一个小旗,那是上一次上岸时做的最高潮线的标志,距我现在的位置大概有...一百二十米。哪里的沙滩估计都有这么大,我去不了罢了,再说第三次海平面上升事故以來,就很少见到活的人。有时候在家里远望,偶见些许孤零零的人影。然而没登上去往埃塞俄比亚的人类方舟的,都是不知死生的人影。
现在我想更新一下小旗的位置,坡不陡,却绝对漫长,小旗的位置可能刚越过坡面的中点。沙泥交界处的路往往最难走,软的地方更软、硬的地方却不硬。 我一步一步缓缓地走着,时时抬头远眺,极目之处是一座连续刚构薄壁墩大桥的起始口。尽管是刚构,混凝土外表的被潮汽侵蚀得厉害。原本这是一座普通的跨江大桥,现在也摇身变成跨海大桥了,数不清的壁墩像旋转木马一样坚硬,而将来它们会像旋转木马一样上下浮动,毫无目的。不久便到达了小旗那里,旗上表面倒是较为完好,除了,
三个疮孔。
怎么来的孔?大概直径两厘米的孔,切割口很平整——这是不是切割的产物都无法,甚至还有三个。好在并不妨碍它能从泥里拔出再插到新的泥土里去,也不妨碍它能被显眼地发现。我走到高处,大概再高了三十米,坐下来等待涨潮。
退潮一结束就开始涨潮,没有停留的时间。潮水飞升,直逼原先的位置后轻易地超过了它,最后停止的位置比现在还高了二十米。插下,等着小舟轻轻飘过来,回家。
我的家在顺序的第七个壁墩处,准确来说是第七对,两个约七米见长五米见宽不知多高的壁墩由海底延伸,同样构成了我家的承重柱,大概是一栋三层的平顶水泥楼,外墙灰黑,内里我已装修过。
整栋楼都沒有一扇门以供进出,如果有人想进来也没门,因为日常情况下我全把窗户紧闭,保持语言静默与无线电静默。海浪很强,撞击壁墩的次次都能掐灭微渺的希望。不过在这里住久了,本来就没什么希望,青藏高原都被淹了,除非那登上方舟的几万人共同蜷在狭小的乞力马扎罗山顶,否则还不如像我一样白白生活着。
驶舟浮行,就算是现在(傍晚)也能见到弥天星星,还有洒了的牛奶。牛奶的旋臂向东北、东南各伸出一条——从二十三年前第一次海平面上升以来很多大城市都停电了,这样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能看见橘灯一般的星星,有时白天也能看见比太阳还亮的光点,距离很远罢。
之前跨出来的窗户还开着,进去之后把舟尾的绳束系到家里的立柱脚上,这样舟想跑也跑不了。以前夜里睡不着时听着涛声滔滔撞击壁墩,舟也在上下上下地腾止,它低声说:“能不能别牵着我?”那天夜里我拒绝了它,自那之后它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诸如此类的话也一并消失了。不过它驶着还是挺称心如意的,没什么可抱怨。
翌日早六点.海浪的固定闹钟将我叫醒。独居生活像瀑布一样直来直往,晓寺奔马。洗漱、做早饭,这种日常大概持续了一年多了。早饭是煎鸡蛋、色拉、煎香肠,我不知道这样平和的生活能持续多久,油、米之类的厨房家什不见一半,也没有零食、饮料,唯二充足的就是电力和水。太阳斜照时,壁墩底下平顶那面的太阳能板便可利用。由于就一个人,电力总绰绰有余;水可以就地而取,放到外墙的蒸馏箱里,不出一小时便可集滿四百毫升,家旁的浮筏上固定一些岸上的黑泥,泥上种青菜、白菜、土豆、番茄之类的家常。通讯设备倒是有,不过静默了。平日里以阅读、锻炼消磨时间,也想过出海的事,但最终还是一次又一次自我否定。
我细嚼着香肠,想着今天该读哪本书,带着餐盘上到三楼,可算作一个小图书馆,里面堆着一叠叠的书,没有次序可言,没有新旧之分。其中一些是海牛商队送来的,他们会在闰年冬天时滑着海牛在结冰的海面上运送人类需要的东西,去年冬天时我发现了他们便点火拦住了,他们得以知晓没登上方舟的人,竟然没死,或许就我一个。我摸着海牛砺灰粗糙的脑袋,另一只手腕上系着一粗麻布袋生活物资,其中大部分是书。向他们再三道谢后,便滑冰回家,在路上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到海牛“吁哞”的叫声,我知道它想在海里而不是在海上,然而这仅是我一种善解人意的刻板行为,我想,或说希望它能成为我的宠物...载具...或者朋友...马上到来的冬天我得遂了心愿,时间不多了。
那里有一本完全沒印象的书,名叫《斯普特尼克恋人》,作者是村上春树。好熟悉的名字,感觉五十年之前极其具有分量,他没得过诺奖?我查查。
二零二九年诺文得主,村上春树。其获奖作品为《驾驶我的车》。
这说明我的感觉是对的,他获奖的时候距今五十三年,现在估计早就化为一堆粉末而进入名人堂了。我不由得怀着一点敬畏开了这本书。
还没看完第一行,窗外传来一阵敲窗声。还得让我下楼,心想。一边把餐盘拿起顺便带到厨房,打开窗,眼前竟是一位五六十岁的男人,东亚面孔。偏胖而身高适中,看起来能谈笑风生的样子。稍显衣衫不整,进来后踏了踏脚,整了整衣服,正眼对我说:“看看吧。没关系,我有时间。”
“看什么?你是谁?”
“《斯普特尼克恋人》。后面那个问题不那么重要。”
“一个陌生人闯入了你贫穷的生活,你会不想知道他的名字?”
“贫穷是一种幻觉,就好比我只能天天在海上吃蛤蜊煎,这算不上贫穷。况且名字仅是一个附属物,你明明可以有更多的,‘笨重海草’‘卫星恋人’......不管怎么样,这本书并不厚,就算你在一口井里下坠那么短的时间你都可以看完。”随后他坐了下来,不再看我,我只得阅读,还是别想太多了,我想。
当午时,便看完了。其间我偶尔需要休息休息眼睛,便眺向向窗外,通过余光能看见男人也在眺望,口中吞云吐雾被海风带至窗外同空气相较量,时时念念有词,而大多我听不清内容,他仿佛知道或者预料到什么时候我能读完,也在此刻缓缓转向我。
“这本书,怎么样。”这句话听着有些古怪,感觉是光了喝了酒中冰而滴酒未沾的怪异。
“很好,让我想起了《我爱你》,余秀华的。”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好......我还想起《远乘会》,三岛由纪夫的。那位母亲的恋态之爱,竟跟《斯普特尼克恋人》中堇和敏的同性恋有打通之处。不,我并不是说同性恋变态,我只是说这些爱情在这个蛮荒年代,太少见了。再说这本书创作于九十年前多,我并不了解...”
“没关系,我推崇三岛的《潮骚》那样的爱情。那这本书中斯普特尼克式的愛情,你怎么想呢?”
“驾驶我......”
“我不认为是那样的。”
“情书。”
“嗯......”
“可是岩井俊二,他并非与三岛同时代吧?再近一点的村上春树,和他相比都稍显老态,叶中真显、小林泰三兴许和他一样都是二十一世纪的名家。他编剧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也很喜欢,和《情书》中的爱而不得不同,莉莉周像是爱之必得,却不知代价。难道斯普特尼克爱情是说像情书里面两个藤井树,遥不可及吗。”
“确实,爱情本来就遥不可及。”他接上我的话,很完美地,满屋续上连杯的沉默,他缓缓开口,“这样,我讲个故事。”
在海平面还未上升的时候,天神山诊所接受了一位癌症晚期的青年,与其说是诊所,不如说成那些大医院无从下手的“累赘”的收容所。青年名叫知念庆,日本人,住院时二十一岁,具体资料尚未公开。他自称自己绝对没有患癌,身体仍然健康,然而被扔进天神山的大多数都安乐了,当时我是他的主治医生,到最后到底起什么治疗作用我也拿不准。
或者......根本没有作用
他是一个从事艺术专业的东大三年级生,他系里的同学无一不评价他对色彩有极敏的直觉。这种天分,是被同样的天分“联觉”赋予的。联觉,是你看到 一段文字,就把这段文字所呈现的复刻在脑海里,细节越真联觉越强。“看不见的也能看得见”,这句话是他的社媒上的标语。
我第一次扫描他的身体时,看到他的癌已经扩散到整个上躯。我告诉他他的时日不多,两三周也不一定,他却说他能预料到他死时是什么样。这样的话对医生来说很吸引人,我便问他:“什么样?”
他不语,只是指指大脑。“什么意思?”
他不语,离开了诊室。莫非是指他能预料到死状是因为联觉?三天后,他开始莫名其妙地哭,他自称为“癫哭症”,起名灵感来自于华金菲尼克斯饰演的小丑所患的“癫笑症”——不明不白地便会狂笑,随时随地,他看书时会发作,看喜剧时会发作,连什么都不干望着窗外也会发作。他感叹,什么话都感叹,而这些感叹的文字又像3D打印机的启动指令,在他脑海里起舞。
“只不过是电信号的传导,别研究了。”他对戴在头上的电波检测仪略有不满,“村上医生,您结婚了吗?”
“并未。”我略微考量文字问题的可行性,“你呢?”
“本有一订婚的女友,她说等我出院就结婚,现在恐怕不久就天人两隔了。”他脸上先是浮现了一些幸福的表情,眼角亦有些湿润,右手不自然地卷着刘海。而接下来竟发作了,看起来像是又笑又哭的样子,脑电波激烈地回荡起伏。怎么办,如何停止联觉?癫哭症百分之七十是脑电变化太频繁导致脑部受损引起的。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哪个表情在代表他的想法。他总是似乎在和什么半推半就,过了一会儿,他有平复的迹象,而后逐渐稳定。
“我和女友同为东大学生,那之前我是以全日本第一的成绩考进美术系的,有些名声也算正常。我和她初见面她说我古板奇异。”他脸红道,“而后的情节有些俗套,但凡恋爱大差不差都经历过,幸福的日子持续到逛美术展时我忽然晕倒的2056年7月12日。醒来时她守候在病床边,看起来几夜没睡,此时已酣然入睡了,我能想象出我昏迷时她的模样,而我停不下来。
“被告知罹患癌症,我当即要求出院以度过余光,尽管医院里的谁都不同意,唯独我和她同意就够了。她这个更古板奇异的人用轮椅将我送了出去。随后借住在她家里。”
我觉得他说的哪里有些不对,这更加加深了我的疑虑,但现在不是提出问题的时候。于是我听完了他和女友的经历,期间他仿佛早有预料似的没有发作,此种预料感时有滋生,令我感觉他是可控制自己的。
待他离开,我在诊室里停留了一下午,我怕感觉出错,又怕亲手毁掉他的人生。怕放任他他又会自寻了断。话说我本也有一婚约,同医学同事的,但出了意外,最后转移到天神山的时候没能救活她。其实我该下定某种决心,最终留给我无尽的遗憾,笼罩着山草的暗涌。她死后由我全额支付医疗费用,改动的不过案本上的几个数字,而又再向外界证明天神山的地位与能力相符——反正也救不活几个,那不如名正言顺一些,执行安乐吧。尊重病人的意愿,随时待命。那之后不常想起她,因为她是我最无法忘记的人。
翌日,他在我桌上留了封字条,上面写着:“今晚来找您,请抽出时间。感激不尽。”
晚些时候,他果真出现在诊室门口。
“村上医生,明天上午8点执行安乐好吗?”没等我同意,他便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谢谢。”
他便离开了,我松一口气,看来我不需要揭穿他了。此刻又传来敲门声,还是他。
“您会同意的,对吧。”说罢他却又哭起来,截然不同于癫哭症发作时的哭泣,感觉此时他的眼泪像是太平洋上的雨滴。
“知念,你......”
而他似乎不想听到接下来的东西,真正地离开了。
临近注射时间第二天,我敲开他的房门,我原期待看到一个完整的人形,而在病床上的只有一颗被水封的大脑,大脑连接着各种仪器,在没有营养、氧气供给的情况下仍然呈现着脑电波,表面的沟回有三处平整的创口,好在并无大碍。
我全然不明白他的用意,隐约觉得他以另一种“想”存活下来,而......
“而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故事讲完了,“你觉得他想干什么?这里的爱情又如何呢?”
这个故事如电影浮现在我脑海里,我觉得很困惑,我不得不望着窗外思考。
“或者我应该问:‘知念庆,你想起来了吗?’”
一整个海洋的错愕向我袭来。
当我醒来时,天花板的全息日历显示今天是某年的春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旁边守着的是村上医生。
“村上!我的女友呢?她在哪里?”
“刚醒别乱动,她在来天神山的路上。摘除大脑的手术很成功,你再也不会联觉、癫哭了。”
我不适宜肝肠寸断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
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春天
一本熬过冬天的春天
我想回忆起和女友的种种过去,却总是残缺与空白的上升海平面。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零重力科幻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0gsf.com/a/17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