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蝰蛇
责任编辑:烫烫
本文获得第八届衬衬杯科幻征文二等奖
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是恐惧,而其中最强烈者是对于未知的恐惧
——H.P.洛夫克拉夫特
1.
第1037日,我勉强穿上舱外服,跛着步子走出飞船。
身前是46光年,身后是无限远。
我降落的地方是一片低矮树林的边缘,星罗棋布的小池塘散在草地上,我摘下舱外服的手套,试着感受草的触感——沙沙的,当我抬起手来看的时候,发现有绿色的颗粒掉进了掌纹里。
我不知道这一切因何而开始;也许是因为在只有石头和阴风吹过的孤寂行星上发现那只巨大的、五彩斑斓的鸟,也许是窥见了那片足以令任何正常的头脑发疯的诡异星云,也许只是——这片泛着暗紫色背景的天幕,和外面寂静的深空一样令人绝望。
这里古老到难以想象。无人机检测的结果告诉我,这颗比任何已知岩石行星都要大一圈的星球从三亿年前的大融合中幸存了下来。
不应该在这里的!不应该!我应该立刻回到飞船上,头也不回地逃跑!
我跌坐在池塘边缘凸起的岩石上,摘下舱外服的头盔,双手胡乱地抓着头发和脸。这是到达遗迹之前我最后的机会。
曾经有56艘旅行者飞船到过这颗星球,无一例外是“归根”计划的志愿者,无一例外都没有离开这颗星球。
我沿着树林的边缘散步,在一下午的时间里接连发现了三艘飞船——它们的锈蚀程度各不相同,船体上爬满红色的藤蔓,悉悉索索的小生物在它们复杂的机械结构里安了家。飞船的标号分别是13、24和55,根据扫描仪的显示:13号旅行者飞船在3200万年前与共和邦联失去了联系。
我对这里发生了什么完全没有概念,这个宇宙中人类无法理解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哀嚎星云的边缘通过最后一个卡哨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常人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想象的宇宙恐怖。
黄昏降临的时候,我看到了它。这个古老世界行将走向死亡的太阳把最壮丽的光芒毫无保留地洒向行星,在天幕紫色与暗橙、明黄交接的地方,色彩斑斓的巨鸟拖着红色的尾羽冲向远方的群山。我劈开蓝绿色灌木,斩断眼前的红色藤蔓,看见那块斑驳的厚石板斜插在潮湿的泥地里。
以前的报告提起过这个东西——Sprox纪念碑,在尚有文献记录的年代被远疆科考船在milkdromeda(1)科学家预计在40亿年后,在本星系群中两个最大的成员星系──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之间会发生星系碰撞。对于这一合并后星系的命名有多种提议,其中最广为接受的是“Milkomeda”,亦即“银河系”(Milky Way)和“仙女座星系”(Andromeda)的英文合称。内域的荒芜星球上发现过。
我僵硬地站在原地,双腿完全不听从大脑的调遣,我就这样从日头西垂直站到三轮明月依次升上头顶,看到那石板上弯曲的字迹开始在夜幕下发出幽兰的光。我晕了过去,向后倾倒的身体重重地撞在石碑上——充满敌意的宇宙终于向我摊牌。
2.
我最后一次走在“巨锥”的过道中,从训练区徒步走回1G重力区休息。巨锥的每一条廊道都十分开阔,呈三角形结构互相支撑,构建起了这座大小仿若行星的建筑物的骨架,廊道两侧排布着数以千万计的房间,每走几步就会看到一个与廊道的顶棚同样高大的三角形感应门。我闭上眼,感受着橘黄色的顶灯和感应门上形状各异的红色线条,它们简单的颜色在我的眼底汇聚成千万种色彩的洪流。这样跃动明快的颜色令我心慌,使我难以克制地期盼着早些离开。
1G重力区的丛林城市是仿照我的家乡——边地的泽雷明都建造的。在从边地前往这个坐标严格保密的邦联总部时,我在邮船上读到了有关巨锥的信息:它并非人类建造,不论从外形还是科技形式上看都绝非出自人类之手;邦联政府在由于某种同样严格保密的原因退居到milkdromeda边缘的时候发现了这座废弃的建筑物,即便是现在,巨锥上仍有46%的区域从未有人探索过,而这座仿造的泽雷明都就是利用这样一块曾经无人问津的区域建造的,专为第98期“旅行者”任务的飞行员——我训练所用。
我讨厌我的家乡,但此刻我却舍不得这处仿制品。在那个真正的边地星,我的父母在我五岁时离异,我在父亲永无止境的暴力和咒骂中苟且生存到十岁,才被所谓的“人才师”发现,他对我父亲讲到了“难以想象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被选中参加了归根计划”之类的话,这些是我对于自己身世唯一的了解和印象。
我乘坐藤蔓梯回到自己4号叶上的树屋,屋子的四壁覆盖着摇曳的绿色茎蔓和叶子,房间中弥漫着木头的香气。我看了看桌子上摆着的一沓纸,封面上用通用语写着“归根计划的其他特殊说明”,我懒得去看其中的具体内容,草草翻过前面冗长的安全守则部分。册子的大半都在讲过去的97个飞行员怎么怎么样了,在哪个地方失去了联系——其中一个高频出现的坐标是在前些年的学术期刊中常常出现的,距离目的地仅一步之遥的名为“古”的星球。我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手指被一个完全陌生的名词喊了停,那就是那个即将给我带来无限的恐惧的名词;我坐上桌子的一角,细细审阅着这一部分的内容,关于这样东西的描述极其模糊:
“内域勘探舰队发现的某种...”
“年代几乎与所在的星球一样久远”
“...造成四名队员精神分裂”
“...请勿靠近...在有异常感的星球尽量不要离开飞船。”
异常感。
3.
可怕的分裂感究竟从何开始呢?我在漫长到不可思议的旅程中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什么呢?
也许这所谓的“分裂感”——小册子中描述的“异常感”,自旅程开始时便已寄存在我心中,只等待那几次与纪念碑的不期而遇将这感觉释放。
在飞船进入一号跃迁域前,我看见巨锥插在那颗蓝绿色的气态行星正中;这个诡异而宏大至极,超乎想象的巨型组合体给我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压迫自巨锥向我席卷而来,古老的一号跃迁域门户开放时,再通过触显看向巨锥,那光怪陆离的神异景象足以令最伟大的神智学家发疯——纷杂繁乱的线条和光线从触显四周向中央伸展,聚合成无数的螺旋,四散溢出的空间泡遮盖了整个画面,巨锥和它所攀附的行星幻化成一团蓝绿色和银灰色混杂的光晕,只能看清大致的轮廓,这轮廓占据了四分之三的屏幕,仿佛不可名状的,来自无限遥远之地的完全陌生的伟大神明,超乎人类的理解,超乎人类的想象,只要窥见一眼,我可悲的灵魂就会为它所癫狂。我想起小册子的第一条安全守则:“尽量避免在进入一号跃迁域前从飞船观测巨锥。”
我的确因为违反了这一条而晕倒在驾驶座上。醒来时,哀嚎星云卡哨的工作人员正准备往我脸上浇凉水。我从床上坐起来,两边的工作人员静静地等待着。我的脑子似乎又开始工作了,但很不妙的是,我发现自己不再能控制自己的想法——现在我的第一意识同时告诉我两个相反的意愿:
应该立刻逃跑,立刻回到生我养我的邦联星域去。
在这里领通关文牒,然后头也不回地冲进前方的无人深空之中。
我无法做出选择。
“先生,先生?”我发现自己塞着耳塞,工作人员说话的声音我是通过耳塞听见的。
我正欲拔掉这烦人的玩意,几个穿着绿色制服的边检员就冲过来把我按倒在床上,其中一人吼叫道:“你是疯了吗?就算你还没有,只要你摘掉这玩意,哀嚎星云也会让你发疯的。”
我扶着床沿下了地,那两个相互矛盾的念头仍盘桓在我脑海中;而此时,更多相互矛盾的异常想法正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即将崩溃的神经。就在这时,我来到了视野开阔的弧形舷窗旁,迎来了哀嚎星云赠予我的第一份大礼。
卡哨位于哀嚎星云的正中央,从这处嘲弄一般的观景舷窗中向外看去,墨绿色的哀嚎星云翻卷成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螺纹,盘旋着直插向无限远处,而我所在的位置正是这个巨大海螺壳的最深处,空间由广阔变为幽闭,压抑到令我难以喘息。
我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在哀嚎星云卡哨休息,于是我在卡哨错综复杂的走廊里来回穿梭,试图赶走脑子里那个应该“不正确”的第二人格,但它扎根之处似乎也在我脑子的最深处,而在生命的前二十六年一直居住在我体内的第一人格则只是大脑边缘的一个旁观者。在一成不变的走廊里,我迷了路,站在十字路口的闸门前不知该向哪处去,四外不见人影。这里令我想起一个几乎与这星云一般古老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那位五十三亿年前的宇航员与我此刻的处境又是何等类似呢?面对着某种完全未知的东西,处在距离文明几乎无限远的深空之中,在这宇宙的螺旋深处一个极度幽闭的空间里,面对比这幽闭恐怖得多的无垠。
在这绝望的当口,我顺着走廊的金属墙面蹲坐下去,用手捂住眼睛,试图去思考——思考自己当下的处境,而千头万绪最终依旧汇成那两个想法:
逃跑
继续向前走
不知什么病态的想法操纵着我的双手,它们狂野地伸向我的耳朵,把耳塞取了出来。
那声音向我袭来,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那是一种单调至极的宇宙背景音,声音并不大,但是那种令人诧异的单调感和重复感无疑是它最可怕的部分。低沉的,自宇宙诞生之初而来,直到热寂也不会停歇的单调杂音,螺旋状的古怪结构——这就是外域人不敢踏足的,人类世界与“内边疆”之间的最后一个守夜人哀嚎星云。我想:也许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我开始不断地呕吐,根本没有重新带好耳塞的力量和理智,直到因为体能消耗过大和过度惊吓再次晕倒。当我睁眼时,发现自己躺在飞船的自动医疗舱中,船载人工智能告诉我:现在的坐标距离外域边界170光年。
4.
驾驶舱里,橙色和绿色的圆形指示灯分布在这个狭小空间中的四面八方。此时的我已经完全记不起这些指示灯的用途。除了这些之外,只有一盏门灯亮着。各型各色的仪表盘、粗制滥造的星图以及显示着日期时间的触显环绕在我的三面, 偶尔发出一阵轻微的响动。
我从驾驶座上站起身来,拖着虚脱的身体走向舱门;我的身体滚烫发热,命令我立刻找个地方休息——但这只会让我慢慢因虚弱和缺水而死。这忽然让我意识到一个可怕的现实:那个我无力控制的第二人格正试图杀死我——在哀嚎星云拔下耳机的指令就是第二人格发出的,它如今已经攻陷我的大半思维。我本能地把手探进壁柜去摸索食物,一个环状的小按钮出现在壁柜深处,我按下它,电脑提示我飞船已经开始烹饪了。现在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半,驾驶舱上方的一个小虚拟现实仪翻了下来,在驾驶座附近播放11空域星际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今夜有料”,而我向来对这些东西没有丝毫兴趣。
我慢吞吞地坐在折叠桌前吃着晚饭;味道也许还不错,但我的嗓子里仿佛堵着什么东西,难以吞咽。就在我收拾碗筷的时候,驾驶舱里播放节目的声音戛然而止,我竖起耳朵来细细听着驾驶舱的动静;过了几秒钟,飞船开始说话了:“即将进入跃迁隧道,为确保空间泡活动正常,生活舱观景窗将开启。”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一阵嗡嗡声便在四外响起,金属舱壁缓缓上升,露出飞船外面那漆黑一片的虚空。我顾不得拾掇桌子上的一片狼藉,慌忙地冲回驾驶舱,让厚重的滑门在身后紧紧地关上。
我重重地喘着粗气,一下子清醒了不少。空间正在驾驶舱里的环形视窗前折叠,繁星逐渐变成越拖越长的线条,从我身边掠过。进入跃迁隧道的指令绝非我下达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飞船预编的程序。
我今天一定要查清此事。我命令飞船调出所有编订指令的数据,从头到尾细细检查了一遍起飞前的所有预设命令——根本没有这一条,从来就没有跃迁隧道的事。我的额头已经开始冒汗,哆嗦着点选了“最近命令”这一项。在这个条目里,只有一条信息:
五分钟前 进入12号内域“遗迹”跃迁隧道 坐标内-112-07 类地行星
五分钟前。
我细细咀嚼着这个时间。在这间阴暗干冷的小室里,我的贴身宇航服被冷汗浸湿,紧紧黏在身上。在驾驶舱的某个角落里躲藏着我不敢面对的恐怖,这个东西刚才下达了一条意义不明的指令,让飞船带我去一个完全未知的目的地。
那东西也许就在高背驾驶座的后面,我不敢离开座位,不敢转回头,不敢把脚从垫脚上拿下来。我的眼睛只好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的跃迁隧道,这该死的空间开始旋转,银色的星轨形成了一个钻头形;宇宙没有方向,因此每一个方向上都是近乎无限的遥远,空无一物。
我不知何时再次睡死过去,紧紧抓着内侧的扶手,紧闭着眼睛,不敢让一丝一毫的光线闯入。我再度醒来时,面对的就已经是那颗——那颗星球,内112-07,它曾经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但如今早已被荒弃。
我最错误的决定,就是穿上登陆服,背上氧气瓶,踏上登陆舱,瞄准了那个湖畔。
5.
我降落的湖畔怪石嶙峋,登陆舱的舱腹磕坏了,这是最精密也最易受损的部分。我半躺在湖边的滩涂上,清澈发蓝的湖水冲刷着宇航服。湖水很凉。
头盔与飞船上的扫描仪连接着,一方面帮助我了解附近的环境,一方面让我知道飞船上的情况——我几乎是逃也似地离开了飞船,但第二人格却始终以最恶毒的方式攻击我的大脑,阻止我登上登陆舱。降落的过程几乎让我再度晕厥,在剧烈的颠簸带来的,生理上的难以忍受之外,聒噪的第二人格在我的脑里发出一阵阵尖锐刺耳的噪音。登陆舱与飞船有以太连接,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从显示屏看到什么东西遮盖住了摄像头,但我那时无暇感到恐惧,只是琢磨着如何不吐出来。
现在,即便是想回也回不去了。登陆舱斜插在乱石丛中,细细的苔藓覆盖着这些石头的顶端。表面没有一道接缝的,纯银色的锥形登陆舱融入在这极其原始的情境当中。头顶的天空是高远的靛青色,几缕条状的云遍布其间。
脑子带给我一个新的问题——幻觉,无止境的幻觉。面前的湖给我以生命的感觉,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一只只能用“外星”这个名词来形容的,紫黄相间的奇怪动物就从我手底下的沙子里冒了出来,迅速用它某种更加“外星”的器官用“外星”的方式逃跑了。
“外星”,这是我想到的形容这个地方的唯一一个词。不知道这份“外星”中有多少出自我的幻觉,但足以让我产生幻觉这一点本身不就已经十分“外星”了吗?我又开始拿不定主意了,是困在这个地方,还是回到飞船?这时,我鼓起勇气决定阅读头盔发给我的通知:在我附近不足两公里的地方,有异常的突出地面的物体。
我的腿在刚才的狂暴降落中磕了一下,现在还是一阵阵猛烈的剧痛。我拖着一条跛腿沿着沙滩走动,腿渐渐不疼了,一个巨大的黄色月亮和暗淡的恒星沉向北边的地平线。
“应该回去。”
“继续往前走!”
第二人格一如既往地占据了上风。我把氧气罐从背后取下来,重重地戳进沙地里。我坐在氧气罐上,开始咒骂这颗该死的星球——它奇怪到了极点,每一个细节都令我不寒而栗。这一路走来,我的第一人格濒临崩溃,无止境的幻觉频频出现。它们真实到不可思议,而逻辑又告诉我这些东西不可能存在于此;逻辑显然归第一人格管,而现在它不起作用。
我不想去描述这些幻象,每每想起我都会感到难以名状的恐怖。我坐在氧气罐上看着天幕渐渐低垂,幻象仍然在我四周不断上演。我的大脑产生了某种方向感,每一个看到的情境都会依着这种方向感指向大脑的某个部分。“方向感”是在我看到“巨塔”的那一刻产生的;我头盔上的心率数据迅速地上涨,正像我眼前那座黑色的巨塔拔地而起——它是由无数扭曲的黑色荆棘缠绕而成的,锋利的尖刺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随着塔的高度稳定下来,星星点点的黄色灯光在荆棘丛中亮起,我听到了自己原以为不会再听到的声音——边地星首府泽雷明都的方言,家乡话在四面八方响起,荆棘巨塔中弥漫着烤培罗宁叶和面粉的味道。早已被尘封的恐惧在这一刻被召唤出来。16年前的某一天,我背着书包站在泽雷明都42号塔前,书包里是一塌糊涂的成绩单,一如既往。其他人家晚饭的气味总是让我一阵心慌,因为那个所谓的“家”里有那个我必须称之为“母亲”的人和手拿电烙铁的父亲,正阴沉地坐在简易桌前等我回家: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是无趣的,而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以各种残酷的手段施虐于我便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娱乐活动。就像16年前一样,砰砰直跳的心脏把多到超负荷的血液向大脑输送,透过头盔面罩的反光我看到自己的脸已经涨成青紫色。血液冲开了一条从未被开拓的路径,直抵大脑中某个尘封已久的区域;眼前的巨塔开始向地面收缩,如它出现时一般迅猛:黑色的扭曲荆棘,橙黄色的灯光,晚饭的气味,泽雷明都方言——这些东西在消逝前迅速沿着新开辟的通道涌入大脑的那一部分,明确地指向我的第二人格,方向感产生了。
在我坐着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开始记录所谓的“异常感”。在第一栏我写上了“外星”这个词,这便是“异常感”的最直观表现。而接下来是“幻觉”,在我并不十分清楚“异常感”之所指时,我权且将内-112-07星球所带给我的一切感受如实记录,以它作为异常感的范本;一个细节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颗星球曾经有一个名字——索拉里斯(2)是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创作的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小说以一个被神秘大洋覆盖的星球为背景,这个大洋是一个胶质构成的生命体,它能够进入人的大脑,将记忆深处最不为人知的部分,以具象的形式呈现在人眼前。在这片大海面前,任何人都毫无秘密可言,心灵深处的痛苦被袒露无遗。科学家们围绕这个不解之谜做出种种推测,却难以自圆其说。,在一个叫作索美尺度(3)衡量一颗行星与地球的类似程度,如海伯利安的索美尺度是7.9的衡量标准上分数高达9.8,但这里完全没有人类活动过的迹象。我拿着触控笔发了一阵子呆,才咬牙写下了“恐惧”这两个字;我接受了这个事实:一切的幻象都是我内心恐惧的具象化,它们代表着我最想埋藏的过去和我最不愿意面对的未来。
天已经黑了。黄色的月亮只余下一点点亮光,而两个青色的月亮从南方升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月亮是否也是幻象,因为这两轮青月与边地的月亮如此类似。我今晚懒得继续前进,就地放下了自动帐篷。我以最快的速度在一块礁石上解决了生理问题,然后紧紧锁住帐篷的所有入口,只留下一小块窗户。我在帐篷的一角挂起了三角形的纸灯,柔和的灯光瞬间充满这一小块空间,我的被褥铺在地上,也被染上了橘黄色。这让我的内心稍稍平复。我决定不再去探访那个“异常突出地面的物体”,明天就打包回到飞船上,一口气飞到几百光年以外再停下。
这整件事情再蹊跷不过了——莫名其妙的跃迁,目的地就是这颗莫名其妙的星球。我开始继续思考“异常感”的问题:我是在哪里看到这个词的呢?这成了当下最令我迷惑不解的问题。标准时间晚上十点,我准时躺下,看到帐篷天花板上有一根绳子。出于好奇,我拽了一下绳子,一本白色封面的小册子掉了下来:《“归根”计划宇航员安全守则》。我在最后的那几页再次找到了“异常感”这个词,它与一样我从始至终没有勇气去面对,甚至不敢去想象的东西印在了同一页上——Sprox纪念碑。
外面开始打闷雷,大气中的氡被电流击中,发出阴森的红光,透过猫眼射进帐篷里。它跟我在同一颗星球上,相距不过千米。
6.
我在头盔的数据库里检索了“索拉里斯”,那是黎明时代的文艺作品中一颗星球的名字,一个会思考的大洋遍布其上,能够幻化出人类所想之物。
清晨的阳光被云层折射成粉红色。我的目力所及几乎可以达到远方怪石丛生的起伏山脉,脑子异常地清醒,两个人格都躲在大脑的深处默不作声。我没有看到一个幻象,海面上的晨雾渐渐散去,居住在滩涂之中的小生命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
我第一次看到了Sprox纪念碑——它就那么突兀地立在那里,比海岸边常见的斜着生长的怪异石块高出数十米。它的周围空无一物,连石头都不敢靠近这难以置信的造物。我缓缓地向它前进,怀着穆斯林进入麦加一般的心情,走向纪念碑。但大脑坚决抗议着我的行为,它发出阵阵嗡嗡声,阻挠我靠近这建筑。在它面前不到十米的地方,我停了下来——这就是Sprox纪念碑,它仿若来自数十亿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形状粗糙而不规则,表面上篆刻着古老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时而如游龙走蛇般蜿蜒相连,时而简略到用圆圈和点表示,它与任何人类理解范围内的语言都毫无关联可言,正如建造它的那个,早已消失的文明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异族,字都用某种蓝色的颜料涂满,颜色光彩如初,亮得扎眼。这块巨石给我一种异常的感觉——这是真正的异常感,这颗星球上其他的一切与之相比,都像是孩子在玩过家家。
我伸手去触摸那古老的表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的情感对于两个人格还是有一定的束缚作用,它们仍然默不作声,容许我在惊讶与敬畏之中勘探这碑体。在石碑靠近大海的一侧,我看到了那处浮雕——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它雕刻的究竟是什么题材,但浮雕传达的信息无疑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快跑!”
我试图在此描述浮雕的样子:一些类似翅膀的东西布满了浮雕的上半部分,而三个月亮显然是这颗星球的景致,在地面上有一个或是不知多少个某种东西在四散奔逃——这些形体完全无法用词语描述的东西,即Sprox纪念碑的建造者,对这颗星球上的某样东西充满了恐惧。
就在这时,那个击溃我最后防线的东西出现了。在群山的背后,某种东西显出了它的脊背。起初我以为是某个月亮逆光升起,但在不到五秒的时间里,这个“月亮”张开了背部的羽毛。一只巨鸟——没错,一只巨鸟,它的羽毛涵盖了光谱上的所有颜色,全都恣意地向四周张开,跟它相比,那座巍峨的山脉完全是个玩具。巨鸟的翅膀从身后展开,我看到那螺旋状的纹路——和哀嚎星云一模一样,和巨锥行星的风暴气旋一模一样,那是宇宙的纹路,那是一切。巨鸟火红的喙在火红的阳光下张开,它发出鸣叫,腾空跃起,遮盖了原本光芒万丈的苍穹,这鸣叫即是哀嚎星云的声音——这是宇宙200亿年的绝唱,一切在这亘古不变的吟唱中生生灭灭。它就是一切。相比之下,人类数十亿年的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这就是宇宙让我来到此地的目的——宇宙的意识借助这颗星球做了决定,让我身处此时此地。
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双腿跪倒在地,摘下头盔,开始发出怪异的哀嚎,应和着巨鸟的鸣叫。我用尽力气尖叫着,用长时间没有修剪的指甲疯狂地挠着自己的脸,直挠得两手沾满鲜血。巨鸟仍然盘桓,巨大的阴影仿佛覆盖一切。
最可怕的惩罚被巨鸟的爪子从我大脑深处揪了出来,第二人格再也无法找到它自己的位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各异的人格充斥着我;那是人类数十亿年历史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他们举着石斧砍向猛犸象,在缝纫机前劳作,躲在战壕里伏击纳粹的坦克,畅游在虚拟现实构建的天堂里,乘坐第一艘星际飞船冲向深空......每一个人都成了我,我成了每一个人。
巨鸟仍然在天空中盘旋。宇宙就是它,它即是这个空空荡荡的宇宙——唯一的存在,在熵的洪流中等待死亡的巨响。
尾声
我再次醒来时,已是深夜。这里是“古”,第1038日。我已经航行了46000光年,只剩下46光年的路程等待着我去完成。
但我做不到。
即使我做到了,这也是毫无意义的。每一个到达此地的宇航员都知晓这一点——宇宙本身像一只巨鸟一样混沌而愚笨,丝毫不会怜悯,丝毫不会在意。它所做的只是让我们领略渺小,让一切胆敢离开自己蜗居的蠢蛋被自己折磨死。
我一步一步跨进树林,把头盔和氧气瓶甩给Sprox纪念碑。我又是我了——本我,而本我将止步于此。
树林的尽头是一处悬崖,一条热带河谷铺展在悬崖下方。这里就是天命所在。
我不再让脚用力抓住地面,而是任由重力带着我的身子轻飘飘地向河谷坠去。我看到星光璀璨,我的无人机绿色的航标灯在夜空里闪烁。
这是我,这是我该做的。
我还是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所有人。
© 本文版权归 蝰蛇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及合作请联系作者。
脚注
| ↑1 | 科学家预计在40亿年后,在本星系群中两个最大的成员星系──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之间会发生星系碰撞。对于这一合并后星系的命名有多种提议,其中最广为接受的是“Milkomeda”,亦即“银河系”(Milky Way)和“仙女座星系”(Andromeda)的英文合称。 |
|---|---|
| ↑2 | 是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创作的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小说以一个被神秘大洋覆盖的星球为背景,这个大洋是一个胶质构成的生命体,它能够进入人的大脑,将记忆深处最不为人知的部分,以具象的形式呈现在人眼前。在这片大海面前,任何人都毫无秘密可言,心灵深处的痛苦被袒露无遗。科学家们围绕这个不解之谜做出种种推测,却难以自圆其说。 |
| ↑3 | 衡量一颗行星与地球的类似程度,如海伯利安的索美尺度是7.9 |
原创文章,作者:viper01,如若转载,请自行联系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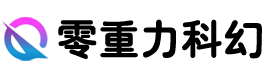
“人最原始的情感是恐惧,而其中最强烈者是对于未来的恐惧。”在这篇作品中你不仅能感受到犹如《遗落的南境》系列带给你的紧张和不安,你还可以看到《索拉里斯星》《太空漫游》等众多科幻名作的影子。